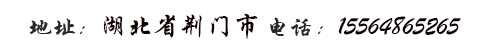故事姐妹们,和摇滚乐手谈恋爱,他真的会渣
|
珊姆的 我叫珊姆,一个普通的美国女生。 我家,美西部的尤里维奇小镇,往西四十公里就是纽约城。 我最好的朋友,尤里维奇学院的女王。 我的知己,一个可爱的咖啡豆男孩。 我的生活,囊括以上所有,依然是朴实无华,像一条平稳奔涌的河流。 只有一次,那么一次,成为了摆脱了我控制的意外——四年级的返校舞会夜,一系列改变的导火索,我喝醉了酒,做了一件尴尬的事情... ------------------------------------------------------------- 1.我始终没能想起来四年级的返校舞会那晚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只记得我穿了一件漆黑的礼服长裙,脚上踏着坡跟靴,裙子和靴子都是从我妈琼斯那借来的。朴实无华,一如既往。大概我那天唯一值得一看的就是去年夏天在维多利亚的秘密买的半杯bra和丁字裤,可它藏在长裙下,一点也不会外露。 当然,别想歪,我那天晚上没想和谁搞出什么风流韵事,我只是觉得有趣,最死板的舞会穿搭,和最性感的内衣,我就爱搞出些有趣没意义的事儿,赛琳娜总觉得我不把注意力放在同类男孩身上而觉得我脑子进水。 除了是我最好的朋友外,赛琳娜·狄弗洛更为重要的身份是——蝉联两年的返校舞会女王,那意味着她是滨河镇最受欢迎的女生之一,是尤利维奇高中实际上的支配者。实际上她不该蝉联两届,因为只有进入高年级才能被允许参加返校舞会。 但赛琳,她总是与众不同。 现在想起来,那都是一年级的事了。赛琳因为和保罗·普拉多在操场角落亲热而名声大噪,保罗·普拉多那会是四年级,尤利维奇橄榄球队队长,尤利维奇高中女生的梦中情人,据说他专心于学业和橄榄球队,长时间内没和谁传出过绯闻,所以你可以了解他和赛琳被人群发现在后操场那棵歪脖子树后拥在一起热吻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 之后的那半年,赛琳快被各式各样的霸凌给整崩溃了,一些女孩的嫉妒,更多的人艳羡她也冷落她。但后来她却因祸得福,意外成了舞会女王竞选得票数最多的女生,当然,大部分投票来自于男生。她那时甚至只是个二年级生,可她站在高台处笑着的模样,就像排练了上百遍,每一个唇角翘起的弧度都恰到好处。那年她的火爆程度在保罗的球队拿到返校周橄榄球比赛的大满贯后达到顶峰,在她甩了保罗之后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每天都有人在男厕所的墙上刻“我爱赛琳”几个字,然后毫不掩饰地刻下署名,这几乎成了某种仪式。 时间一转,我们都已经四年级了,大学的最后一年。 这是我来过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返校舞会,可这和第一次一样无聊。赛琳已经早早地站在了台后,她非常重视这次舞会,毕竟这是她上学时最后一次成为舞会女王。她今天穿了一身华伦天奴的奶油白礼服,戴了她家祖传的一套首饰——祖母绿宝石项链和耳环,非常耀眼地站在台后,和同样竞选女王的贝基·雅利安那说着话,谈话的空隙间还趁贝基看不见时指着她朝我翻个白眼。我回了她一个无奈的笑,看着她又去进行“社交”。 和那边暗流涌动的台后社交不同的是这边的座位区。我正和韦恩坐在一块儿,他是我的舞伴,去年也是,前年也一样。 韦恩、赛琳和我是一同长大的,青梅竹马的情谊和找不到舞伴的尴尬使我和韦恩在每个必去不可的舞会或者派对上都凑在一起结伴,赛琳则大部分同卡梅隆·里奇一道,有些时候则会换换口味带些大学男生过来。我不在意英俊的舞伴、免费酒水、鲜花气球、暧昧的氛围以及五光十色的打光这些“派对”玩意儿。通常情况下,舞会的进程都一如既往地无趣。我会和韦恩选一首不那么难听的歌来跳一曲舞,然后他会送我回家,我在家看我的书,他在家捣鼓他新淘来的计算机或者其他书呆子为之狂热的玩意儿,一切都非常一如往常,不会有任何意外。 但你永远、永远不该指望你可以安排好什么,然后相安无事地过日子。那晚舞会赛琳再度赢得女王皇冠后,我喝了两杯她胡乱调配的鸡尾酒,然后断了片。 2、再睁开眼的第一反应是头疼,喉咙更是干的要命。我睁开眼坐起身,发现那条黑色的长裙没了,身上只有一套维多利亚的内衣。这里不是我的床更不是我家,我凭借我回忆里的画面认出这是韦恩的房间。 门被打开了,我赶紧裹紧了身上的毯子,鼻腔瞬间袭上一股味道。韦恩的床上有咖啡豆的香气(我怀疑他打翻过咖啡在床上,不止一次),他也总是穿咖啡豆一个色系的衣服,“他整个人就是一巨大的可可豆”,赛琳曾这样说过,但她从不知道韦恩只喝咖啡而不是可可奶,而她在高中二年级之后就不太在意韦恩喜欢什么了。 韦恩开了门,却没有立即进来,我听见他的脚步踌躇了一会,然后传来他的声音:“珊姆,你醒了吗?”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因为眼下的情况,不得不说,有些诡异。我想问点什么,但鼻子却闻到了门口传来的浓郁的香,一瞬间嘴馋占了上风。我咳了咳,说道:“你先进来。” 韦恩推开了门,一脸犹豫的样子,眼神躲闪着什么,我只好先开口说道:“韦恩,我渴了。”他闻言抬头,看到我裹在被子里后走了进来,手里正端着一个小狗形状的马克杯,开口的地方在狗狗的脑袋上,可爱中带了点恐怖。他当他把杯子放在我手心里的时候,一股阿华田的香气冲到鼻腔内,棕色的咖啡上漂浮着几多白色棉花糖。 “我接你回来的时候你衣服湿透了,你家里没人,也没问出你身上有没有钥匙什么的,我只能先带你来我这。”他一边说一边坐在了桌子边的木椅上,他耳根突然在橘黄色的灯光下显现出了点粉色,然后语气突然不顺畅起来,“你的衣服,额,是艾玛帮你脱的。我可什么都没看见。” 也许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曾和韦恩一起洗过澡的缘故,我没觉得古怪和尴尬,反而觉得他害羞起来的模样很有意思。我啜了一口马克杯里的阿华田,他加了足够多的奶,一瞬间感到口中甜香四溢,一下子暖到颅内,温暖偏热温度也恰恰好。我看着杯子上可爱的斑点狗,又看着乖乖坐在一边等我喝完阿华田的韦恩,突然觉得诡异地重合起来。 气氛变得温柔而静谧,我默默地喝着阿华田,边情不自禁观察起了韦恩的房间。韦恩的房间和我小时候来到这里时有了些出入。这是一间空间适中的卧室,温暖而干燥,空气中总是可以捕捉到咖啡的香味。墙壁是拿铁色,就是你可以在星巴克买到的那种栗子奶油拿铁同样的颜色,在美国西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带着浓厚的视觉系暖意。 视线游移到了墙壁上,那里挂着的相框里是韦恩和他家人在某处海滩上的照片,隔着相框半米的地方贴着披头士乐队《佩珀上校孤独的心俱乐部》的专辑封面和艾伦·图灵的照片,曾经的这里挂着我画的第一幅画,我记得那是我亲手挂上去的,象征我们交下的“永恒友谊”。有两面沿着墙壁贴合的窗,此刻百叶窗帘高高得拉起,银色的月光铺满了桌面,美丽而温柔。 书桌上方的大部分空间都被巨大的英特尔电脑占据着,靠在一张巨大的木椅边的是一把fender吉他和一把我认不出牌子的紫灰相间的贝斯,书桌旁满是划痕的大理石桌上摆有很多笔、尺子和刻刀,我记得他的手工课总是能拿到A+,桌子边的书柜最上层也摆满了小雕塑和刻板画,很精致,但有不少都蒙了灰。他的书堆里多了不少我没看过的书,甚至还有几本我认不出来语言的外语书,书柜上面摆着一堆的绘画工具——是了,韦恩是一个校园漫画杂志的主编来着。我突然意识到我对韦恩·麦克弗勒的了解已经像赛琳一样浅,除了每年的舞会时间,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 我突然感觉到遗憾,为我儿时和他约下的信誓旦旦的“永恒友谊”,为长大后轻易地失去童年的那些珍贵事物。 “我完全不记得我醒来之前的事了。”我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房间里的静谧,脑子里仍然一团浆糊。韦恩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眼睛里透着一股子忍俊不禁。他松开一直揪着毯子边缘的手,然后清清嗓子:“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但我简单地概括一下好了——你喝醉了,然后和一个三年级男生当场热吻,他的舞伴将一整盆桑果汁混伏特加倒在你的身上。” 我愣住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手里的马克杯倾斜得几乎要把阿华倒出去。韦恩连忙扶住摇摇欲坠的马克杯,唇边却挂着幸灾乐祸的笑容:“你真是一战成名了,珊姆·塔尔顿。” 我出声问道:“那个三年级男生是谁?” “艾萨克,艾萨克·李,打赌你一定有所耳闻。”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倒在枕头上,感觉自己的头又隐隐作痛起来。 艾萨克·李,俊美无双的三年级生,新一届尤利维奇女生的梦中情人。传闻和他那双在钢琴、电吉他琴弦上都能畅快奔走的手握上一握就能获得一个月的幸福心情。我现在是真的有点恨赛琳——更恼怒在她递来酒杯时一饮而下的不计后果的自己。 喝完了一杯阿华田之后的我已经被这个夜晚折磨的困倦不易,不知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清晨被洒在脸上的阳光唤醒,我睁开眼睛,看见韦恩房间两面巨大的窗,透明玻璃任由着金灿灿的光线溢满这个房间,一瞬间使人感觉站在阳光的中央,温暖到热烈。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早晨——被阳光唤醒。空气里残存不去咖啡豆香味诱惑着你往床的更深处陷。正当我转个身打算再赖一会床时,韦恩的侧脸突然爆炸在视线里。脑子里就像冲了个凉,连带着昨晚的宿醉都清了个干净。我意识到昨晚我没有回家,还跟韦恩睡在了一张床上,我感觉我毯子下的皮肤立刻灼热起来。 老天爷,老天爷!怎么回事? 3、阳光真的很好,但我真的很紧张。 厚厚的天鹅绒毯子下,我感觉我的身体发热了起来。我还是只有那套维多利亚的秘密相伴身上,韦恩衣服齐整,仍旧是那件咖啡豆色的宽松卫衣和长牛仔裤。他躺在毯子外,似乎是不小心睡着在这里,嘴唇冻得发白,显得他本来就白的发亮的脸更有点苍白的味道了。我心里一动,轻轻将毯子盖在他身上,然后蹑手蹑脚跨过他的腰,那一刻我想的竟然是,这张床真是柔软的不可思议。 下一秒就发生了悲催的事。床实在太软,我站不稳脚,一下子趴在了韦恩身上。这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事情了。韦恩睁开迷惑的眼睛,在看到我之后迅速侧过脸移开目光,一下子暴露出了红的彻底的耳垂。 我讪讪地从他身上趴下来,新买的维多利亚半杯已经皱了起来,但还是能遮住我的胸部,我慢慢曲起腿,放慢掩饰的动作,希望使自己更自然一点。韦恩明明看见却要装作没看见,我突然有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想法——一时兴起穿的x感内衣也算是有人看了。 毯子又重新被盖回到我身上,我们俩坐在原处,半天没有说话。气氛僵直着,我忍不住要迟疑地开口,他却抢在了我前面:“我已经跟琼斯打了电话,她知道你昨晚住在我家了。” 我松了一口气,有点感谢他的转移话题。他起身,从床头拿来一件浅灰色的羊毛衫:“我昨天晚上就想拿给你穿,但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睡着了。” 我抱歉地笑笑,接过厚实的羊毛衫。韦恩转过身背对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我坐起身站在床上,拆掉羊毛衫的吊牌——这还是一件新衣服——从上而下套下来,非常宽松,刚好遮住我的大腿。 “我好了。” 韦恩转过身来,我看见他眼睛里有什么情绪闪烁而过,很快就不见了踪迹。他自然绅士地向我伸出手,韦恩的手干燥、温暖而且柔软,连纹路都是那么细致。我任由他牵着我走下床,套上他大大的蓝色棉拖鞋,然后跟着他去楼下吃麦克弗勒夫人做的百吉饼加煎鸡蛋。 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的时候,大卫·道恩朝我喊道:“明日之星大驾光临了。”我无视了那些人或调笑或幸灾乐祸或不明所以的目光,径直走向了赛琳的车,她正靠在车门旁和卡梅隆说话,脸上的笑容有些放荡,这对于一个正常的清晨来说有点过分,但我想也许是昨晚的舞会王后和卡梅隆的床上表现让她性欲高涨。 赛琳看见了我正朝她走来。她推开正要吻她的卡梅隆,高跟鞋踏在柏油路上的声响快速且清脆,我跟她照常来了个拥抱,我闻到了香奈儿的丝滑甜香味儿,可思绪却不受控制起来,一下子闪回到昨晚被咖啡豆拥抱的温暖感觉。 赛琳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念想。她夸张地说道:“说真的,昨晚是我12年以来,最为你感到骄傲的一晚。拜托告诉我你昨晚有跟艾萨克·李睡觉,拜托!“ 我挣开香奈儿的怀抱,顺便一巴掌拍在她脑袋上:“别告诉我你居然还有脸问这个。你忘了昨晚是谁递给我的自调混合鸡尾酒,才两杯我就不是我了,你觉得这很好玩?” 赛琳一点都不生气,反而一脸笑意。她推开了再次凑过来的卡梅隆,新上任的橄榄球队队长面色不善地瞪了我一眼,我无暇看他,赛琳已经瞟见了从一辆银灰色保时捷上下来的艾萨克·李。她大叫着招呼他过来。我暗骂了一声,转身就走,我猜我颇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 “嘿,”有人在叫我,我步子更快了些,“嘿,等等!” 走廊上已经有不少人在看我们了。我一头扎进文学课教室。梅利先生还没到,教室里三三两两坐着几个人。身后的“吱嘎”门一下,我绝望地看着艾萨克·李推门而进,然后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教室里的声音骤然小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注意力已经从他们自己的谈话转到了我和艾萨克这里。 我无奈地看着艾萨克,双手抱在胸前:“嘿,这里是四年级的文学课,我想你不适合呆在这里。” “不碍事,”他笑起来,伸出右手,“艾萨克·李,昨晚和你接吻的人。” 我听见教室里的人抽了口气。 我没有和他握手。我转过身来正面朝着他,用上了我最诚恳最体贴的表情:“艾萨克,我很抱歉,但昨晚我喝醉了,实在是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有个好建议,我认为你像我一样赶紧忘了这事儿,这对我俩都有好处。” 他的笑容淡了下去,语气似乎有点怨气:“你不能这样,塔尔顿小姐,这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过去的问题,你昨晚上舌吻了我,你听到了吗,是舌吻,法式的那种”。 我猛地怒上心头,刚想发火却又有些心虚,不由自主地避开了他眼睛投过来的视线。教室门在这时又打开了,赛琳和卡梅隆一同走了进来,跟在后面的是韦恩。我顿时松了气。 赛琳一眼就看见我和艾萨克坐在一起,她的眼睛放光,快速地朝我眨了眨眼。我将目光放在韦恩身上,他穿了一件黑色的帽衫,这么冷的天气也不穿外套。他走路的样子总是带着点随意,我注意到艾萨克将目光放在他身上,然后站起身来,极其自然地向韦恩招手:“嘿,贝斯!” 我困惑了,连带着赛琳和卡梅隆以及其他人都迷惑地看过来。这真的不怪我们,你知道,艾萨克和韦恩,实在是难以搭在一起的两个人。 韦恩是那种可以在二年级一整年都穿咖啡色上衣和运动裤的人,他对电脑有着超脱常人的热爱,他还是《怪形》杂志的主编,就是那个全校怪胎都会去看的杂志(当然也有例外,我也会买来看韦恩画的怪物,但我不是怪胎)。艾萨克是校园摇滚乐队的主唱和吉他手,他英俊得可以连载在校报的封面上,每个月都会被邀请去记者部做采访,我敢打赌半个尤利维奇的女生都会把他刊在报纸上的照片剪下来贴在自己的卧室墙上。但这样不同的两个人却站在一起打着招呼,这场面几乎有点诡异。 梅利先生走了进来,清了清嗓子。艾萨克拍了拍韦恩的肩,目光悠悠地掠过我时顿了一下,然后径直走出教室。韦恩坐在了被艾萨克移歪的椅子上,正要从包里拿出书本,却在我古怪的眼神中败下阵来。 “你想问什么?” “为什么弹贝斯?我记得你弹吉他的技术可是比起那位艾萨克不遑多让。” “别乱讲,”他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笑容,“艾萨克的乐队之前的贝斯手转学了,他们也只要贝斯,我想做出点改变,就去面试了。” 我点点头。早在艾萨克叫他贝斯的时候我就猜了个大概。突然我又觉得好奇起来,我侧着身,靠在桌边,看着韦恩将书和笔摆在桌上。他做这事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格外的从容,和我们这个年纪急躁的青少年很是不同。 “韦恩,”我叫他,他转过头来看我,一边注意着讲台上的情况:“什么?” “我可以去看你们乐队排练吗?” 他看了我一眼,说话时突然磕磕巴巴起来:“我们...额,我们现在还没能写出什么歌,你知道,艾萨克开始组乐队也才半年,我们还在翻唱,没什么特别的。艾萨克可能不会喜欢女孩子来看排练,也许下次我可以去问问他。” “乐队叫什么名?” “毒蛇屋。” 我看到韦恩窘迫的表情,不禁露出笑容。梅里先生咳了又咳,我终于停住了追问,继续听艾伦坡美学分析。 4、返校这段时间,最典型的公共活动就是返校精神周。但返校精神周在我看了几乎就是神经周。 约定俗成,大家会在星期一穿黑色,你走在走廊里会觉得自己在参加穆斯林葬礼; 星期二整个校园就像回到了五六十年代,男生穿尼龙西装,女生穿颜色靓丽的蓬蓬裙,韦恩一如往年,把头发剪成55年左右约翰·列侬(披头士乐队主唱、吉他手)那样的飞机头,贴着长鬓角,一副teddyboy的模样。但他走起路来的摇摇晃晃和他微笑起来时乖顺的模样却更像可爱的保罗·麦卡特尼(披头士乐队主唱、贝斯手),他总会因为两不像被大家嘲笑; 星期三穿印第安人的衣服,这更显得非常讽刺。 星期四时男生和女生互相穿彼此的衣服,这对隐藏身份的gayfriends是一种安慰,对我来说只是穿着常服,我的卫衣通常会选择小码的男装,那让我觉得舒服,但经常有人误会我穿男朋友的衣服,呵呵,“男朋友”,我不想解释,这样的谣言每次都会在韦恩带我来舞会时不攻自破(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会觉得韦恩是我那个“神秘的男朋友”); 终于到了最后一天,星期五,制服日。大家会穿上尤利维奇校徽上的铁锈红制服衬衫,男生黑色西裤,女生黑色中裙,那一天的校园会异常的平均和正常,除了赛琳和其他别有心思的女生会一如往年将裙子拉高到腰部,她说“那既让她的胸部看起来更加挺拔,又能露出更多的大腿,”我无可厚非地点头,套上黑色皮鞋。 返校周最后的也是最狂热的项目,也就是橄榄球比赛开始前的时候,我又见到了艾萨克·李。 由于返校舞会晚“睡觉”的缘故,这段时间我和韦恩的关系拉近了不少。最近我都会在赛琳不在时和韦恩呆在一块,这几乎快让我忘记了返校舞会上的“亲吻事件”。迪尔菲尔德学校的野狮队进场的时候,我和韦恩坐在了第五排靠走道的位置,赛琳是啦啦队队长,她站在最靠场内的中间位置,方便卡梅隆赢球之后奔跑到场边和她接吻。座席区入口处的艾萨克注意到了我们,他高高地招了招手,然后朝我们走来。他在铁锈红的衬衫外套了一件牛油果色的皮夹克,诡异的配色却显得这个人明亮新鲜,像一篮子里最漂亮的那个水果。他走近和韦恩打招呼的时候,我看见他在胸口别着“我爱尤利维奇”的圆形支持徽章,他手里还拿着一个袋子,里面全都是这样的徽章。把徽章递给我的时候,他的目光直直射向我的眼睛,就像《X战警》里的镭射眼斯科特与敌人对战。随后他很快微笑起来,气定神闲的语气让我不由自主觉得不舒服:“你好啊,one-nightkisser.” 我别开视线,偷偷看了眼韦恩。他瞟了这边一眼,然后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专注地看着下方的场地,双手插在兜里向后靠。艾萨克似乎完全不在意我没有理他,反而紧挨着我坐在长条凳上,将一袋子徽章放在脚边。 我有些烦躁,于是假装没他这个人存在,专心看比赛开场前的啦啦队舞蹈。赛琳的裙摆上下飞舞,露出蜜色的笔直的腿,流畅的肌肉线条随着动作而舞动着,我的目光追随,然后看见她朝我遥远地抛来一个飞吻。 有时候我真觉得,尤利维奇没有传出我和赛琳是对蕾丝边这件事,真是个奇迹。 我们今天和滨河镇另一个高中——也就是迪尔菲尔德私立学院的野狮队——打友谊赛。说真的,回顾两个学校打比赛的历史,大前年是迪尔菲尔德获胜,前年是尤利维奇,去年又是迪尔菲尔德,今年大概又轮到我们,命运的天平似乎哪边都不偏,的的确确是友谊味十足的。 我心不在焉地嚼着薯片,看见卡梅隆赢回一球。尽管大家对比赛结果都心有猜测,但场上的轰鸣声还是几乎要撕碎深蓝色的天空。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尤利维奇队的里昂以扭伤一只脚腕为代价将那椭圆的球扔进李维斯的怀里,力气大到几乎要在李维斯胸膛上开个洞。李维斯倒在圈内,裁判吹响哨声,整个尤利维奇的人一同站起来身,打翻了放在腿上的薯条和可乐,大声欢呼着鼓掌,艾萨克高喊着“bravo”,我怀疑他是想把自己肺里所有的空气都用来欢呼。韦恩则站在椅子上,似乎是想看清楚里昂的伤势。大家目睹着卡梅隆·里奇高举着双手围着球场奔跑,然后飞快地冲到赛琳身边,一把将她举起来放在怀里拥吻。座席上的欢呼声立刻变成了起哄的唏嘘声,我情不自禁笑起来。韦恩从椅子上下来,将手伸进我的薯片盒子里,一把拿出来了五六片:“送你回家吗,还是你想去哪里走走?” 我刚要回答,就被旁边的人拉住了:“你想不想去看国王酒吧转转,我今晚在那边驻唱,顺便可以帮你点一杯混合鸡尾酒。” 听见“混合鸡尾酒”的时候我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转头看见艾萨克弯着嘴唇调笑的模样,才后知后觉他在开我玩笑。我瘪了瘪嘴,余光看见赛琳跟我招手,然后拥着卡梅隆离开。我戳了戳等在前面的韦恩:“送我回家...” 我还没说完就又被艾萨克拉住了手臂。此时的座席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群在往外涌,经过这边时他们都会多瞟几眼。韦恩站在我身前替我挡住目光,我不耐烦地冲艾萨克道:“你到底想怎样?” “我是只想带你去一次国王酒吧,仅此而已。” “但我更想回家。” “我可以送你,拜托了我只想唱首歌给你听而已,答应我吧,你不必喝酒。” 我看了眼韦恩,他双臂抱胸,背对着我们。艾萨克注意到我看向韦恩的目光,笑着拉过他的肩:“贝斯,韦恩,拜托,劝劝你的青梅竹马,让她跟我走吧,就半个晚上就好。” 我看向低着脑袋的韦恩。他前几天刚剪的列侬头已经长出了一点新的绒毛,看上去柔软得像初春时的草地。他目光游移着,眉头不自觉地皱起,我的目光似乎让他不适,他一直不看我。艾萨克软磨硬泡着,最终他还是缓慢点了点头:“珊姆,艾萨克确实很想跟你聊聊那天晚上的事”,说完他飞快地瞟了我一眼,不等我回答便继续道,“记得早点回来”。我看着他转身离开,心情不由自主地低落下去。 我坐上艾萨克那辆保时捷的时候被贝基·雅利安那看了个正着。我拉上车门后透过车窗看见她咬牙切齿的样子,和她平时的淑女形象有些出入。艾萨克明显也看到了贝基,更明显的是他踩油门的速度,似乎是在逃离什么是非之地。 我好奇地盯着倒出车位的艾萨克,他似乎对贝基有点避之不及。他注意到我的目光,主动开口解释起来:“抱歉,贝基是我的前女友,我不想她毁了这个晚上。” “为什么分手?” 说真的,我不是故意这么直接,而是实在没心情去做委婉的对话。不过艾萨克似乎也不拘小节,他只是看了我一眼,夜晚的街边路灯照亮了他宝石一样的瞳孔,我注意到他翠绿的瞳孔颜色和他的牛油果色夹克非常搭。他耸了耸肩,一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点开车载的音响:“那天晚上你拉着我打啵,贝基跟我大吵了一架,我觉得我无法再和她继续下去了。” 尽管不想承认,但一股愧疚感还是从我心脏里生长出来。音响里放的是杜兰杜兰乐队的歌,车窗外的人们来来往往,我小声说了句我很抱歉。 “你什么?”他故意靠近我,眼睛里闪着的笑意过于明显。我深呼吸了一下,然后冲着他耳朵大声道:“对不起!我不该强吻你!” 艾萨克闻声笑了起来,一时间一星期以来对于那天晚上的莽撞举动的懊悔,人们的调笑打趣嫉妒的背后言语,以及,韦恩的回避,都在他的笑声里化成了烟气瞬间散掉了。那笑声真是爽朗极了,像秋天的风,能把心头所有的郁郁给吹散。 车行驶到山路边时,他一脚踩下油门,银色的保时捷在夜色里飞驰起来。我被惯性带的后靠在座椅上,伸手拉开了车窗。冷风涌进了车里,我伸出一只手,感受风的力量。我突然想起不知在哪听过的有趣理论,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你知不知道,当你把车开到八十迈的时候,把手伸到窗外,风带给你的感觉就像在上一个D杯本垒打。” 艾萨克挑挑眉,嘴边的笑容就没有消散下去过。他没说话,继续踩油门,也将靠窗的手臂伸出窗外。我们开在无人的笔直街道上,我看到表盘指向80,手里的风就像有了实物。我趴在车窗边,时不时把头伸出窗。风力实在过大,一下子吹散了我盘起来的头发。之前染过的暖橘色头发缠在车窗边,又顺着风梳散开,又缠绕又散开。杜兰杜兰的主唱Simon在音响里大声宣告着“MOREJOY!”,艾萨克朝窗外的夜色大叫着“哇——噢”,到了几乎破音的程度,我怀疑我嘴边的笑容是被巨大的风吹的翘起来的。 我感到一种快乐,从胸膛里炸开来。夜色里冰凉的风和银白的光能驱散你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里的憋闷。我想像艾萨克那样高喊,可我只能微笑。Simon又一次唱“MOREJOY”的一瞬间,我们同时将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然后看向彼此。对方实在是过于秀色可餐了一点,我舔了一下嘴唇,没忍住,凑过身去亲了一下艾萨克的脸颊。 车速慢了下来。男生的手伸到我的脖颈后面,我的皮肤感受到了一股凉意。我看见艾萨克近在咫尺的绿色瞳孔,玫瑰色的嘴唇平缓而坚定地靠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内的画面突然闪回到舞会那晚的第二日清晨,我趴在了韦恩的胸膛上,他迷迷糊糊地将手放在我的背上,然后呆楞地睁开眼看我的样子。 我记得他的手温暖而干燥,放在我的背中央,热度一下子从脊骨灼烧到大脑。 订阅解锁TA的全部专属内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eiguihuaa.com/mghfz/11801.html
- 上一篇文章: 故事校花轰动全校,富二代砸钱狂追享受了
- 下一篇文章: 感悟春运佳句,耐人寻味,值得反复品读,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