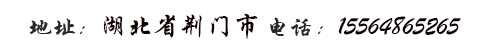我的家族迁移小史一
|
我父亲原来姓易,胡姓是后来从南京到延安去,地下党的黄楠森(北大哲学系教授)给他改的。也是父亲的继母的姓。 我们这一支易姓的祖宗原籍山西太原府,元末避难于滇、后入川。在四川富顺赵化镇的九云砦乡聚族而居。在大石母有一个易姓宗祠,每年清明节,当地易氏摆酒席几十、百把桌,祭祀祖先。九云砦是一个建造在石岩上的大山寨子,这是族人为了躲避“棒老二”(明火执仗的强盗)的避难所。我的的祖父大家庭住的地方叫“官儿咀”,是一个由两个四合院组成的砖瓦结构的大宅子,有正房、厢房、花厅等大小房屋几十间。背后是一幅茂密的青杠林的山坡,前面即沱江。 沱江是四川四大河川之一,两岸丘陵起伏,江面宽阔,水流平静。父亲从小在江边玩水,练得一身好水性。所以后来我们兄弟都从小会游泳。前两年,我每到一地,必找地方下水,无论是江、河、湖、海。非典前的一年,在北京小汤山宾馆开会,偌大的一个标准游泳池,就我一个人孤独地游来游去。 祖父是川大前身成都大学政治系的首届毕业生。校学生会主席,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成都学联主席,曾带领学生冲进当时四川省教育厅长万克敏的公馆。文革时,我也曾“带领”造反派一卡车的人冲进贵州省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的公馆,那年我十一岁,正坐在家门口玩,被手持武器头带钢盔的人叫住,问贾公馆在哪里。那些年头,为革命者带路是光荣的。 祖父才华横溢,不仅英雄爱美人,聚了校花为妻(祖母胡佩玖,中文系生,后来成为我的国学启蒙老师),而且一毕业就被张表方(张澜)任命为成都蜀华中学校长。硬是将一所很差劲的军人私立学校,造就成了一所成都青年人人都想读的名校。他的理想是办成上海中学、扬州中学、甚至南开大学那样的风气的学校。可惜他三年之后即积劳成疾患肺结核而英年早逝。张表方挽辞“志宏而气锐,心细而貌魁,宜其腾达于政治,而仅以办学试其才。江安以之病,蜀华以之死,吾惜乎斯人之遽逝------”云云,凭此语知祖父真长得帅。后来查近代报刊,有一本叫《蜀风》,竟然有他的一大册纪念专辑,学生很多写了悼念文章,写祖父去世的那几天,去家里吊唁的学生前后有二三百人之多,哭啼声、呼唤声,响起在屋子院子里的每一个角落。 祖父有一年夏天在家乡养病,晚风和畅的傍晚,携继祖母与我父亲,包一条打渔船,泛波于星光之下。一边消暑纳凉,一边看渔夫打鱼,打着鱼就呼将来,在船上现杀现煮,其味鲜美无伦。江水清澈,游鱼可数,沱江的肥沱、岩鲤、退鳅,都是父亲儿时记忆中的无上珍品。 中学即能背《莎翁乐府》的父亲,后来同时考取三所大学,两所理工科,一所文科。却遵继祖母之命,择文弃理,念了中央大学政治系。也许继祖母潜意识中要投射她的亡夫想像于父亲身上,可惜她错了,父亲学政治真是决定性的误会。父亲太渴望母爱了,后来就把他的母爱想像转移投射。就这样离开了长江,鞋底里藏着黄楠森给他开的北平地下党城工部介绍信(是一张用隐形墨水写的钞票),历尽艰辛奔赴了解放区。接下来又从解放区南下贵州,从此离开了水,他似乎就永远就失去了灵气,娶到我母亲算是他的最大成绩,大半生好像都过得比较拘谨。 也许是家族命运中鱼水缘还未尽,冥冥之中,大学毕业,我竟跑到安徽长江边的芜湖去念了一个研究生。那年放寒假回家之前,从长江边买了一条齐人腰的大青鱼,腌制风干,提回家给父亲过年吃。记得在汉口轮船转火车,有半天空馀,小件寄存处不存大青鱼,苦了我提着那大家伙,晃悠晃悠,在武汉街头逛商店,把好多售货员都吓坏。可惜拿回去,父亲只嚐了一口,说是“比起我们家的江团(肥沱),硬是差远喽。”次年更行更远,跑到上海来念博士,从此再不离江海之畔。虽然是从沱江入长江入海,可是那气象格局,竟反不如易家老祖一二也。所以,也常常在风和月白之仲夏夜,想像着沱江那一只打渔船,上面坐着我那“志宏而貌魁”的政治学祖父和他的校花妻子,以及清水中可数的肥沱与退鳅。 (原载《古典今义札记》,海天出版社,年版)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eiguihuaa.com/mghxx/10040.html
- 上一篇文章: 城市更新优秀案例推荐成都音乐坊,用音乐共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