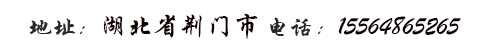魏鹏学弥撒书中的玫瑰对荆棘鸟中人生哲
|
~~一~~如果我们不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上帝纯粹是人造的神灵,是人类苦难者潜意识中精神胜利法的最光辉也是最黑暗的闪现。那么教会无疑充当了它最圣洁的光芒也无法掩盖的脓疮,并以其光怪陆离的谬论向诸多对它卑躬屈膝的人炫耀和说教,尽管在宗教的法衣里不乏圣洁的光芒也无法掩盖的脓疮。可是千百年来,信奉上帝在西方人心中已经形成了深厚的甚至无法割舍的心理积淀,同现实世界相对照,宗教为人们营造的了一个尽管虚无缥缈,但却“圣洁完美”的理想所在,于是,对上帝的爱便成为人们一种高层次的精神寄托。澳大利亚作家麦考琳撰写的长篇小说《荆棘鸟》中的男主人公——拉尔夫便生活在这种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在浓重的宗教氛围中,他对上帝的爱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而漫长与固定的神职道路更使这种爱渗入到他的血液,他的骨髓。《荆棘鸟》中的拉尔夫是英格兰贵族的后裔,从神学院毕业后的二十年里,从事着罗马教廷与澳大利亚教区的联系工作,他忠实于罗马教廷,关心教区人民疾苦,既被教区人民视为精神支柱,又受到罗马教廷的赏识,他的超群才干使得他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都有所建树,因而不断升迁,最终获得罗马教廷红衣大主教的位置。可以说在宗教生涯、神职道路上,拉尔夫未曾遭受过早期同行们经历的诸多艰难,他的博学多才和极其高雅洒脱的形象使凡尘中的大富婆玛丽?卡森夫人也为之倾迷,以至在她去世时,将德罗海达牧场的所有财产遗赠给拉尔夫作为其宗教活动的经费。 ~~二~~ 雨果说过:“在伊甸园与地狱之间,有着世界,在开始与结终之间,有着生命,在超人与最卑劣的人之间,有着凡人。”(1)拉尔夫的悲剧在于他以凡人的血肉之躯选择了超人的艰苦神职道路。玛丽?卡森对拉尔夫超出宗教仪式的爱展开了人性与神性的第一场争夺,在玛丽?卡森看来,拉尔夫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躯身上都是属于上帝的,她看到了一个获着勃勃野心的,矢志追求神职荣誉的男人,她清楚自己的形象无法使拉尔夫这样对上帝忠贞不二的人动心,却还是毫不犹豫地要求拉尔夫爱她,“我要你吻我的嘴唇,而不是仅能表达仁慈之心的手指,拉尔夫?”(2)在常人理性和感性的理解上,玛丽?卡森之于拉尔夫的无可名状,无法实现却有真切存在的爱,是对上帝的第一次挑战。她明白拉尔夫之所以能容忍她对他有凡尘之爱的举动是因为拉尔夫在他的宗教生涯中需要“进身之价”——她在拉尔夫的眼中是拥有物质财富的人,而钱财对从事宗教活动的人是极其重要的。 也许玛丽?卡森在人性上能激起教士迸发凡尘之情的魅力太小,拉尔夫最终没有给玛丽?卡森要求的给她情人一样的吻。尽管拉尔夫屈服于她的慷慨遗赠,在对上帝的忠贞和虔诚上,作为一名教士,他坚守住了宗教的清规戒律。诚如诗人在一滩死水面前没有灵感和激情一样,拉尔夫对玛丽?卡森超出寻常的爱表现出最不友好的态度——称她为“老蜘蛛”。在玛丽?卡森明白她自己无法取代梅吉在拉尔夫心中的地位时,她由女人惯常的嫉妒变成对拉尔夫的爱和恨,这种被激发的情感象烈焰一样无情地焚烧尽了玛丽?卡森精神和肉体中仅存的一丝青春气息,她老态龙钟的脸庞上显示出只有少女才有的红晕。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老年复发的爱情加速了她走向死亡的步伐,拉尔夫的眼睛中根本容纳不下她的丝毫娇态,她开始愤恨,却又无可奈何,在克服不了这种慈母般的恋情时,她突下决心,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遗赠给拉尔夫,她坚信一点,在她死后,忠诚于上帝的拉尔夫会因她的做法而痛苦的,“我现在知道,当我在阳界之外的地狱中被焚烧的时候,你依然留在阳间,但是却在另一个地狱中忍受者比上帝可能制造出来的更为猛烈的火焰的焚烧。”(3)她坦率地告诫拉尔夫:“我始终知道怎样让我所爱的人受苦受难,我爱你,但是希望你在痛苦中尖声呼喊。”(4) 事实证明玛丽?卡森预言式的恨是正确的,拉尔夫对上帝的虔诚使他被梅吉唤起的人性的一面大受挫折,拉尔夫的痛苦在他和梅吉不同寻常的爱恋中最终走向了极致.玛丽?卡森的慷慨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拉尔夫步向理想地位的奢望.他这种全靠个人力量为教会争得的利益是他在教皇面前备受赞赏和青睐,他在教皇的眼睛中看到了希望,便决心将他心中的玫瑰藏匿在隐秘的角落.看到希望的男人(特别是野心家)是可怕的,玛丽?卡森的遗赠给梅吉心中爱的渴求一种悲剧的预兆。 ~~三~~代之玛丽?卡森不可避免的失败,善良、漂亮、多情的梅吉象一块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着拉尔夫的爱心。在梅吉刚从新西兰来到德罗海达牧场时,他就爱上了这个比他小十九岁的姑娘,这种爱最初象一种兄妹式的爱,而随着梅吉的长大,它渐渐演变成一种美丽纯洁的爱情。拉尔夫把梅吉送他的玫瑰花珍藏在他的弥撒书里,“梅吉就是他的玫瑰,”(5)“是他生活中最美丽的形象和最美好怀念,”(6)就这样,弥撒书与玫瑰花构成了拉尔夫的整个人生。拉尔夫没有经历过他的同行们那样的早期的压抑,时代的变化已给拉尔夫这样的人的个人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宽容,放眼辽阔的自然风光,置身和谐的牧民生活,拉尔夫拥有比他的前辈更为健康的身心,但灵与肉的矛盾依然存在,对拉尔夫来说,宗教是他的,更是他命中注定的职业,是他一生前途之所系。他的骨子里有很强的功业欲望,为此,他决心以坚毅的毅力放弃爱情,将玫瑰永远珍藏在心中,但是不管他身在哪里,哪怕是跻身于罗马教廷的中心梵帝冈德罗海达永远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每逢休假回到这里时,面对着梅吉,他总感到“保持灵魂完美”(7)的困难。在经历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之后,终于在梅吉疗养的麦特劳克岛,他理智的力量在肉体的热情中消亡,他与梅吉共同走入了伊甸园,真实的幸福令他反省,“我是一个人,永远成不了神,”(8)“一个象我这样的教士的骄傲是多么的虚假。” 拉尔夫从来没有否定过爱情的幸福,他与梅吉的关系也没有受到来自外界的惩罚,但红衣助教的诱惑再一次使他离开了梅吉,他就这样在上帝和人性之间游走,在权力与爱情之间徘徊,他想两者兼得却不可能,他试图放弃一方,而任何一方都使他难以割舍,他既不能做一个完整的教士,又不能做一个真正的爱人,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中,他竟挣扎到红衣主教的职位,实现了多年的梦想,而回过头来,他才发现这成功毫无意义,为了这最后的成功,他出卖了自己的感情,失掉了亲生儿子,失掉了宝贵的人生幸福,他失声痛哭为自己而哀悼。在德罗海达,疲惫的拉尔夫终于倒在梅吉的怀抱中,声声呼唤着爱人的名字而死去。就象古老的凯尔特传说中胸前带着荆棘的鸟,泣血而啼,直至呕出自己的心。拉尔夫根本没有想到,梅吉的爱情会撕破他对上帝的无限虔诚和忠贞。当小梅吉在懵懂中明白了做为女人的奥妙时,拉尔夫便感到他做为男人的一面正在复苏,“长期以来,他对孤独的梅吉的幸福关怀备至,这使他焦躁不安,辗转反侧,”(10)他感到“在这有感情的人和无感情的神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对比,”(11)他对她的爱和他的教士的本能使他获得了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使他抵挡住了现实带给他的那段难以摆脱的恐惧。 然而,他同梅吉一样,都是时代的俘虏,在坚守着普遍的宗教时,仁慈的上帝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给他的使者指出明确的不能更改的人生道路。拉尔夫在竭力忘掉自己作为男人的一面,矢志如一地为上帝效力时,他感到作为教士在梅吉面前不能象在其他人面前那样从容镇静地进行灵魂的导引。梅吉的成长和人性的复苏强烈地动摇着他忠贞于上帝的灵魂,他不能舍弃其中的任何一方,这使他痛苦万状,而梅吉在他醒目中的美好形象更象丽日的朝霞一样给他不能抑制的人生向往,使他坚固的精神防线出现了危机,但是在他跻身红衣大主教之前,拉尔夫没有因为梅吉的痴恋而放弃当一名完整的教士,就连梅吉心中的渴求——自然的吻别也没有满足她,他象避蜘蛛的毒汁似的躲开了梅吉凑上来的嘴唇,他感到作为一名教士,神性的导引超越着任何世俗的力量,包括作为人的心理渴求,他战胜了人性复苏后,希望过常人的生活而带给他的痛苦,这一次,梅吉和拉尔夫都输给了上帝。在上帝将拉尔夫从她身边夺去之后,梅吉在一种思念和怀恋中尽力地忘却着那些美好的过去,在她感到无法彻底抵御对拉尔夫的想念时,她决定嫁人,但结婚除了给她多添了一条小生命之外,他并没有拥有作为女人的真正幸福,她在失望,痛苦,孤独无奈中重新回到了德罗海达牧场,她开始热烈的怀念过去,(这时的拉尔夫已当上了红衣大主教)直到拉尔夫在人生的极峰之上感受到空落,反而珍视人间的至情时,梅吉才从拉尔夫那儿享受到了她渴盼了一生的幸福,但在上帝的车轮上扶銮的拉尔夫并没有因为梅吉而在现实的道路上止步,他依然告别麦特劳克岛,穿上红衣大主教服为消除灾难遍撒仁慈而到处奔走。这一切对梅吉来说是可怕的,但她拥有了新的生活希望,一个鲜活的拉尔夫的化身——戴恩的出生彻底地改观了她暗淡的心情,当戴恩以完全的宗教热情赞叹和欣赏拉尔夫的辉煌业绩时,拉尔夫还蒙在鼓里,梅吉却看到了又一种不祥的预兆,戴恩象他的父亲一样以更炙热的激情投入到了教区的宗教活动中,这使他惊恐万状,可恶的上帝又要夺取她心爱的戴恩,她试图改变这种即将发生的可能,但在他彻底地了解了戴恩之于上帝的无限热情和虔诚后,她不得不说服自己这是命运的抉择。她决定将戴恩送到拉尔夫那儿接受宗教的洗礼,她尽管憎恶和诅咒上帝,但他唯一能相信和依赖的人还是拉尔夫。梅吉在给拉尔夫的信中写到,“我从你哪儿偷来什么,便还你什么!”(12)这是一次无奈的痛彻心肺的决定,她隐晦地向拉尔夫说出了她心中诸多的复杂情绪,在保持爱心和坚守忠贞上做着无法理解和想象的牺牲。上帝先后从他身边先后夺取了他深爱的两个男人,(拉尔夫和戴恩)她在精神的空落和失衡中承受着拉尔夫也未曾完全觉察的痛苦,在失去戴恩这一件事实上,梅吉的抗争又一次输给了上帝,特别是戴恩为救两个失水女人而献出了他宗教的热情和生命的躯体时,梅吉心中刮过一阵无法排遣的绝望情绪,他不顾路途遥远,依然前去要求拉尔夫为他们的孩子做出走向天国的努力,把戴恩的尸体从异地运回来。拉尔夫在震惊、哀伤中逼迫地接受着一个事实,他和梅吉的麦特劳克岛之行使他在违背上帝训诫的同时,在事实上使梅吉孤独、失意地度过了一生,而他在上帝眼中又不是一名无暇的教士,在梅吉眼中又不是一位完全的男人,在行动上他亵渎了无暇架势的形象,在心灵上违背了人性中自然的爱与恨,他的醒悟是在他失去亲生儿子之后,人性的又一次复苏使他愧疚地倒在梅吉的怀抱里。这是一个凄美悲壮的心灵等待,有梅吉对上帝的控诉才能使我们明白宗教对心灵的戕害是多么地严重:“不仁慈的上帝,除了从我身边夺走了拉尔夫,为我做过什么呢?上帝和我我们互不喜欢,上帝你再也吓不住我了,因为我应该恨的不是拉尔夫,他只是在对你的恐惧中生活者,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值得热爱。”(13) ~~四~~相对于玛丽?卡森,梅吉对上帝的抗争取得了悲壮的胜利,尽管这种胜利伴和着她一生的所有痛苦。玛丽?卡森预言式的告诫在梅吉身上产生了伟大的奇迹,她的勇敢和执着使城府极深的拉尔夫彻底地揭下了他宗教的法衣,在麦特劳克岛完成了作为男人最辉煌重要的一课。在人性上,拉尔夫仅在恐惧和自然的渴求中尝试了生活的甜美;在神性上他却肆恣张扬的用行动表明对上帝的忠贞不二,对拉尔夫来说,不能宽恕的一点是他用爱心唤起了梅吉对他的依恋,却又在梅吉彻底爱上他时,他却依然离开梅吉效忠于上帝。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玛丽?卡森为了她眼中的幸福过早地撒手人寰,梅吉为了坚守她一生的期盼,白了头发,两个女人在拉尔夫面前的执着和坚贞,沉重地动摇上帝在拉尔夫心中的缥缈地位。神职人员毕竟不是神,而是人,在这种厮守和等待中,纵是顽石,也有被感化和醒悟的时刻,何况拉尔夫又是一位感情丰富的男人,只是这种人性的复苏使拉尔夫在忠于上帝和拥有个人幸福的夹缝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将一生赌给了上帝却又没有成为一名无暇的教士。 ~~五~~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宗教现象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宗教对人类的影响也存在着相对的正与负价值的两重性。从宗教的正价值来看,它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出符合人们理想、希冀、安全和生存的希望,提供了助善惩恶的伦理规范,引导人们追求理想的境界,等等。这些也许是宗教经久未衰的一个原因。但对宗教的负价值,人们也看得越来越清楚,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尤其是人类理性精神觉悟后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宗教的黑暗性、蒙昧性、非理性、非科学性被揭露和批判,它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尤其是对人性的严重残害更得到充分的认识。拉尔夫的内心冲突不是善与恶的冲突,而是黑格尔认为最具悲剧特性的善与善的冲突,他在天堂与尘世之间苦苦徘徊,在神所指示的道德与人的自然属性之间无可适从,而一生的不幸经历与结局最终说明了他是人,与神无缘,拉尔夫的形象为人们提供了深刻的认识价值——记住他的痛苦,珍惜我们的生活。考琳的《荆棘鸟》使我们摆脱宗教的神秘色彩,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又一次看到了现实的强大生命力,他以人们惯见的家世小说的形式展示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更刻画出了拉尔夫、梅吉这样不同凡响的艺术形象。当我们赞赏作家的不朽艺术才华=时,不难发现作家在展示人物灵与肉的心路历程上获得了成功。显然,考琳在塑造她心目中的艺术形象时遵循了这样的美学原则——没有冲突的圣洁和省去冲突的卑劣,都缺乏人情人性的丰富性,只有冲突的过程才能展示心灵世界的生动,也只有展示这一过程,才能表现出灵与肉主题的深邃和博大。朱光潜先生指出:“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14)那些本应该但却难以统一的灵与肉的冲撞和厮咬,那些试图躲避苦难最终却承受了无尽苦难的无奈与坚韧,营造出无限的悲剧情韵,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人的情感回应,使人们在领悟生命复杂深刻的同时也得到审美的满足。愿拉尔夫的灵魂安息,愿他和梅吉的悲剧不再重演。 引文出处: (1)雨果《巴黎圣母院》 (2)―(13)《荆棘鸟》 (1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第一次读《荆棘鸟》这本小说是上大学时,看到同学陈宏伟放在枕边拜读,我随手翻了几页,即被其优美的文字和深邃的思想吸引,遂借阅一个月,做了大量笔记,随后去学校图书馆借书,却没有,只好去书店找寻,购得一本,借此完成了毕业论文。当时的中文系副教授黄涛梅给我们教授外国文学,我去请教论文写作,她问我在哪儿能买上这本书,我便送了黄老师,毕业后又买了一本……迩来已有二十三年的光阴,现在读来感觉依然清风扑面,今天转发昔日的毕业论文,是以为念。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eiguihuaa.com/mghfz/9532.html
- 上一篇文章: 瑞香红,雪中红玫瑰,活动倒计时2天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