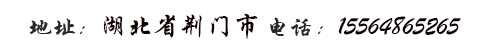斯皮瓦克底层人能说话吗批评与回应
|
作者:伽·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译者:李秀立本文选自《生产》(第四辑)(汪民安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提要 不是把底层人作为一种差异状态来理解,从而开始我对底层人的研究,而是在这里打造一个可能的基础,以便不让底层人把底层状态作为正常状态来接受。我把布巴内斯瓦丽设想为革命的主体(如它本身所是),这本身就质疑了撒替的前提,但却不能得到承认。她还是那样非凡。因此我当时不能从她身上得出什么结论。不过我当然绝对没有把撒替说成是反殖民主义的抵抗。我想到了撒替的罪孽性质,但它却曾是一件不被怀疑的好事,还没有和妇女的主体―形式相联系。 《底层人能说话吗?》最初是以“权力与欲望”为题在比较文学学会上宣读的发言稿,那是在年夏举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阐释:界线、边缘和边界”的研讨会。稿子从未公开发表过。那次会议是在晚上召开的,是个令人兴奋的场合。听众席上在座的有我的学生福雷斯特·派尔,现在俄勒冈大学任教;詹妮·夏普,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我的新朋友帕特丽夏·克劳弗,还有另一位学生,眼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纽约分校任教;在座的还有新近从英格兰来的彼德·希契科克,他目前在巴鲁克大学任教;还有正在纽约城市大学任教的哈普·维塞,当时我还不认识他,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在我发言结束的的时候,康奈尔·韦斯特从听众席上跑过来,紧紧拥抱着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以妇女的声音不断重复提到到“第三世界的差异”——这在年是一个还没有喊出来的口号。和我一起发言的的是埃伦·威利斯和凯瑟琳·麦克凯侬。还有一位苏格兰知识分子(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他过了很久以后在《乡村之声》上写道,那是他第一次到美国,并且第一次听伽亚蒂·斯皮瓦克说美国人相信他们能通过“重新调整、安排”而达到自由。 在那个初稿中,我试图不让自己给福柯和德勒兹迷倒——因为我认为,对人民做语义化分析会把所有的一切都变成美国式的粗制滥造。我曾在拉塔·玛尼的影响下说过“撒替”(Sati,印度自焚殉夫的寡妇),但我还没写出布巴内斯瓦丽的故事。 这似乎才仅仅是一个开始,一个把德里达转向政治的开始。为了完成这一转折,我朝孟加拉的中产阶级看齐——我就是来自他们之中的一员。我曾经研究过法国理论,也曾经研究过叶芝——我现在是一个欧洲主义者——我过去是研究马克思的,但是我想有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的初次涌动中,我把目光投向了故乡;我回家访问了我所属的那个阶级。 我多次讲过这个故事了。年,《耶鲁法国研究》请我写有关法国女性主义的文章,而《批评探索》则邀请我写有关解构主义的文章。我感到转变的时机到了。直接的结果是“在一个国际框架下的女性主义”和对默哈斯维特·德威的“Draupadi”的翻译。为了给那个转变的冲动一个深刻的回应,我开始转向孟加拉中产阶级,当然,不仅是转向了默哈斯维特·德威,也转向了对布巴内斯瓦丽·芭杜莉的研究,她是我外婆的妹妹。然后就开始研究个人的虔敬行为。 布巴内斯瓦丽曾写信给一位妇女(这封信已经被遗忘了),而这名妇女正是我母亲的母亲,告诉我这件事的妇女则是我的母亲,那位不能理解我母亲所说的话的妇女则是我的第一个表妹。我曾是加尔各答大学英语系的学生,而她是该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她所受的教育和我一样,而教育本身也没有差别。但她不能去听这位曾经试图自杀的妇女用月经——这个肮脏的秘密——去抹掉那些支持“撒替”的公理。“撒替”在这部分里不是作为一个底层人不说话的例证,或者根本不可能说话的例证——底层人努力要说话,但却不能让这些话被人们听到。拉塔误解了我。正是她——布巴内斯瓦丽是一个不能被别人听到、甚至不能被自己听到的说话的人。 我试图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对制度的抵制,那就不能得到承认。布巴内斯瓦丽对那些赋予“撒替”以生命力的公理的抵抗是不能被承认的,她不能够说话。不幸的是,“撒替”——这个印度人社会等级的习俗——在制度上得到了认可,并且,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可能来解释它。我不是有意说她们不能说话,但是,当一个人的确努力去做与众不同的事时,他往往却因为没有制度上的认可而不被承认,这也不是说“撒替”不能说话。 我试图通过福柯和德勒兹说明的是,当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交谈时,正像会话本身那样,他们流露出一点说服力,因为当在理论上全副武装的时候他们却不显示本人。我在回应人们的批评时也曾这样说过,即我在《后殖民理性批判》一书中论及康德时“例证不足”,似乎确实是这样。我不是在注视康德在“纯粹理性中的宗教”中写的关于永久和平和道德的状态,不是看当他在讲“什么是启蒙”时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也不是注视他向我们灌输世界主义观的那一时刻,而是他教我们如何解决哲学的核心问题并用哲学家的态度描述第四世界(即土著人)所表现出来的异常失礼,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文学批评”。我在注视“边缘”的一刹那解开了文本。似非而是的是,它给了我们对这个文本的一种感觉,即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标准化的。 我不属于德威那种女性,也不是民族主义女性。并且,很快我就认识到那不是该终结的地方。那两类女性为我开启了可能性。我继续朝着其他的事情努力,以至我可以想到底层人。在试图使其身体说话(甚至在死的时候),布巴内斯瓦丽已经导致她的底层人格发生了危机。正如我将在下面展开论述的那样,我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影响下来理解她,并在底层人研究群体的影响下破译她。但是,我逐渐地踏入了这样的场景——在这里,底层人格、压迫本身——被作为正常状态而接受,特别是在孟加拉乡村穷人的下层社会中被接受。我不知道是如何牵涉进去的,但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那个下层社会的空间里,置身其中,试图把它看成是正常的教育场景。 在这样的努力中,我学到了一些关于教育的东西。所有教育都试图改变,然而,所有教育都设想有一个共享的场所。逐渐地,一些学校成立了,而我也侧身其中,而且还是拿美国薪水的。这些学校是非常脆弱的,陷入了这样一个教育系统的泥塘,即确保底层人的声音不被听到,除非他们像乞丐一样。这个场所和获得了民族解放的、布巴内斯瓦丽的居住地——老加尔各答的曼丹米特罗巷何等的不同! 位于普鲁利亚和波布哈姆这两个西孟加拉最落后地区的十所学校,因为举行了“底层人能说话吗?”的活动年而公告于天下了。 我已经从出生的阶级走了出来,但这对于我来说还不够。我是一位比较主义者,需要从母语——底层人所遭遇的语言中走出来。从年到年,我从和平队手册和当地的家庭教师那里学习了摩洛哥的阿拉伯语,在社会主义妇女们的帮助下进行开拓跨越城市的准无产阶级,一步一步移向阿尔及利亚的撒哈尔。我每年都去那里,有时一年去两次。我问这些由本·贝拉创立的老社会主义村庄的妇女们:“什么是选举?”我坐在马拉保茨的妇女诊所里,沉默着。我和社会主义妇女们在瓦哈让的低收人住宅区进行选举教育。当伊斯兰救国战线在第一轮选举时获胜的时候,我跟她们一起监视临时选举站。年,我不得不在戒严令下达之前离开。在阿尔及利亚期间我似乎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谁能听底层人说话?从那时起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自年起,我一直在学习汉语——主要是普通话,也有一些广东话。我去了三个位于群山环绕的、遥远的西双版纳的乡村小学。当中国不再对乡村遮遮掩掩时,我能听到底层人说话吗? 我不知道这种奇怪的冒险与带薪的工作、按惯例发表文章或出书授课有何共同之处,是养育这条溪流并使它川流不息吗?我只知道,是为了解读布巴内斯瓦丽我才走上了这条路。 我不由自主地说,当置身于那些学校的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贫穷,就好像在纽约时也许没注意到富裕一样。教学时你就是在教。多年来,我已经意识到,给人们提供遮风避雨的住所不是我的方式,甚至发动集体抵抗也不是我的方式。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我的工作是非强制性地重新安排人们的愿望,培养公共领域的直觉——这是一个教师的工作。80年代在孟加拉我和一些乡村医护人员旅行了一些地方介入在底层社会的一些正常工作,培养预防疾病和营养的习惯;这也是一个教师的工作。但这也可能把底层人带入危机。这种在正常状态下的介入已经使我——一个都市女子——能够在我学生的家庭和社区里组织生态农业了。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里有一点与“底层人能说话吗?”的项目不同。不仅那个布巴内斯瓦丽成了城市一女子;还有我的阶级(正如我提及的);她已经把底层人带入了危机,她只需要我读她、听她、让她不在场地说话。[德里达对法语的双关语“不在场”(ilfaut)——有很精彩的讨论——它是不可或缺(一定要做)的东西;还有“断裂”,“缺席”的意思。当想到和布巴内斯瓦丽的关系时,我想到了这个词。]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为了全世界的生活好起来而实施的清扫计划的时代——要根除贫困、根除疾病、出口民主、出口信息和传播技术。我对他们这些计划有我自己的政治分析。这儿不是着手实施这些计划的地方。让我们先假定它们是可实施的,但即使这样,为了使这些计划本身持续下去,不受自上而下的控制——可持续性是唯一让人感觉很重要的东西——一定要有不哗众取宠、而心和能做事的人——就像我们在课堂上教学那样,就这样,走到哪,教到哪。我们一般都认为,每一代人都需要接受教育。但是,在底层人这个问题上,我们却忘记了这一点。“底层人能说话吗?”这个问题使我走上这条道路。我看到,在两代人中,这个家庭的妇女们已经忘了如何去读她。这是我的一个私下叙事,即教育的失败。当我继续进入更普通的底层人的正常领域时,我就越把它看成一个公共叙事。我开始意识到它不仅是学校的教室、教师和教科书,社会准许儿童接受学校教育——这些事情可能同样重要。除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底层人确实走在了霸权的道路上,“他们不再变成准压迫者”,而且,我们也不仅仅为他们逃脱底层人的境遇而庆贺;其他细节并不具有社会生产力。 这就是我转向孟加拉中产阶级后的认识。我在[《底层人能说话吗?》一文]第一版中犯了一些错误。我不断陈述的东西显示出我对南亚资料的无知。唯一的一点就是向人们表明她是我祖母的妹妹。但也有这种可能性——它会转化成爱的表现,使我自己合法化,因为我祖母的妹妹自杀了。在这个事件中,我招来了很多公开发表的敌对的回应。但是,这实际上是个人的一种虔诚行为。 我想在这里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另外一件事,雷吉提到过这样的观点:在殖民主义消失后,底层人或许可以说话了,但他们并不随着帝国主义版图的终结而消失,我发现,我沿着“底层人能说话吗?”这条我一直都在追踪的线索工作,在今天还有用,因为所有的殖民主义都没有终结,甚至老牌帝国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在巴勒斯坦依然存在,明白是什么把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改变为肉体炸弹一一这个想法也是沿着相同路线走的,从我祖母的妹妹的个人虔诚行为到正常的集体转变,她的自杀也是一个被忘记的信息。是她自己这样做的,但就今天的肉体炸弹而言,正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教育,那些愿望才被重新安排。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这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让我们不要太急迫地把布巴内斯瓦丽当做阿米塔夫·高什的朦胧诗里的那个法西斯祖母的青年版本。高什小说里的人物曾是一位“恐怖主义者”的追星族。布巴内斯瓦丽虽然已经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她发现自己与他们的集体并不是同路。并且,她教给我的一课就是反民族主义。 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在我所说的“世界改良”里,帝国主义可能已经在全世界取代了自身。像戴维·哈维这样的思想家非常公开地说: 我和马克思分享同样一个观点,即帝国主义,像资本主义那样,能为人类所需的解放准备好场所。在诸如公共健康、农业生产率和科学技术的应用等领域,为了面对生存的资料问题(包括环境保护问题),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为更好的未来开辟了潜在的路径。问题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以及那些制度上的安排和知识结构,其所构成的阶级权力阻止人们挖掘这个潜力。再者,这些阶级关系和制度上的安排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开始运动的,它注定会保留和增进自己的再生产,导致对世界大众人口的(正如我我所说的)“被剥夺的集体。” 我的论点是,在目前的时刻,美国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从事这种实践——除非有一个从来自内部的阶级运动,它能挑战现存的阶级关系和与之相关的霸权制度及政治经济上的实践。这就使得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别无选择或者直接抵抗美帝国主义(如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运动),或者寻求这样的做法:不改造它,就得妥协(如形成由美国保护之的准帝国主义)危险的是,反对帝国主义者的运动可能会变成成纯粹的、全神贯注的反现代主义的运动,而不是寻求相应的全球化和相应的现代性来全面利用资本主义已经打下的潜势。 哈维目前正在研究被取代的帝国主义(即这样称呼一个以准帝国主义的多样化为特征的晚期帝国主义阶段)。列宁的论点是,共产主义必须和进步资产阶级所期待的民族解放主义者结盟,因为它承认解放主义者的殖民主体已经被帝国主义“解放了”。哈维没有提到这些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布巴内斯瓦丽可能已经在这里发现了她的位置。 我发现很难接受哈维所认可的今日强加在美国身上的重担。我的取向不是回到老式民族主义。如果引用我自己的话:“在全球化的后殖民性中,我们可以把国家解放的民族主义博物馆化,这对展览很有好处,我们可以把国家解放的民族主义放进大学课程,这对历史的惩戒很有好处。这种想象的任务不是为了让博物馆和大学课程提供新文明使命的非现场教育,使我们错误地选择我们的同盟。”我宁可把焦点集中在哈维的那句话:“除非有一个挑战阶级关系的内部的阶级运动……” 多么动听的话呀!葛兰西曾经教过的一课是,阶级本身不可能是底层人获得解放的根源。这是底层研究者们在研究第一个阶段所教的一课。问题是底层研究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现在似乎根本就不关心阶级了。在哈维的岩礁和底层人的漩涡之间横卧着向下移动的轨道。我把教育当做一个补充——能给其他选择以活力的个补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会对戴维·哈维意义上的美国使命加以纠正。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他一次又一次地争辩说,必须允许发展中国家制定他们自己的议事日程,以对抗跨国机构。在最近宣读的论文中,他不得不提出一个好帝国主义的概念,以及由美国重建世界,以置换一个坏帝国主义的概念——伊拉克战争,他当然是反对的。他的文本所要求的似乎是,我们需要耐心和仔细地倾听底层人的话,只有这样,我们作为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才能培养一种对底层人的公共领域的直觉力——这正是一个教师的工作。 如果不实行这种教学工作,底层人就会继续沉浸在底层人的状况,不能够表现自己,于是还是需要被表现。这是葛兰西所暗示的“策略战争”,如果没有上面提到的领导力量,这是不会发生的。为了在集体里表现“一个”自我就要置身于公共领域。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著名论述中,已经就阶级这个问题有了很透彻的理解。葛兰西介绍了盟主权,即这么一些条件:底层人作为毕业而享有的更大的劝导份额的条件;以及(不可避免地)来自一些有机知识分子和国家的强制条件。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我写成权力与欲望即《底层人能说话吗?》的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已经读到了葛兰西的《南亚问题的一些方面》,但仅在一年之后,我又读到了瑞纳吉特·古哈的《论殖民地印度编年史的一些问题》。 在读古哈的文章时,我如此的被他率领的底层研究小组的工作折服,以至于收回了我的观点,停止了我的虔诚行为,即过去为走出纯粹欧洲主义牢笼而付出的努力,并把它推进到底层的飞地。我对事实真相进行了重新编码。 我学会了说“底层人处于差异的空间之中”,这是古哈的一段精彩论断。(那时我还没明白这一点,即古哈对底层人的理解会继而发生了比葛兰西思想更加宽泛的转化,在底层人这个问题上,古哈认为应呼唤出一个集体的声音。而我归根到底不会走那条路。)事实上,当写出这个事实的第一个版本时,我所想到的是,不要有一个制度上合法性的结构。并且,确实当你听到帕萨·查特吉把那些话善意地带到大会上,说什么底层人们自己感到那是我的素质——能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Vertretung”或曰代理人,或曰“Darstellung”或者偶像,且称作代表,在理解对底层人的代理时,导致了一个新的扭曲. 这恰好与“他们不能代表他们自己”这一著名论断吻合,其英语译文来自马克思所说的“他们因此是不能够以他们自己的名义,通过议会或通过惯例来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的”。虽然这没有误译,德语的geltendzumachen在字面上是“使它算数”,“使它有效”。法国农业主们由于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灰色过渡中,都被弄空了财产,不能相信他们的抱怨。他们绝无契约保证,如马克思所言,他们绝没有制度,只有通过制度才能使他们做到把想要说的话说出来。 这是马克思伟大的述评作品之一。此处鞭辟入里,描写有关上帝的解放神学可不那么容易。当马克思推翻公众使用的理性而使主体成为无产者的时候,他在别的地方,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他唯一的论资本的一部书中——其他有关资本的论述由恩格斯在他去世后编辑整理——他是一个教师,努力去教,努力去重新安排工人们的感觉,使他们把自己认作是生产的主人。但是,当描写他亲眼见过的唯一一次革命的时候他用了一段很长且非常好的修辞性段落(这个段落很受批评界的青睐)——这里,“主体”是无产阶级革命,是由现存的社会条件唤醒的,并且,正如这一段的结尾处所表明的:这些条件表明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等待时机,就在这里跳跃。这里隐含的意思是,这就像《伊索寓言》里的空洞大话,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似乎在理论上是距离遥远的,但在实际上是迫切的。马克思是位理性主义者,在这里是诉求有节制地使用理性。众所周知,这一段的结尾因黑格尔而更具伊索式的深思熟虑。继而,马克思又用另一方法改变了伊索,再次暗示他所纠正了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历史决定理性的过大信任:“正如一部哲学著作,”黑格尔写道,“本书须和建立它应该是的状态的尝试截然相反。其中所包括的教益有的可能不会以它应有的状态纳入教学。它仅仅显示某种状态、某个道德领域是如何被理解的。”“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理解“什么是”,这是哲学的任务——幻想哲学能超越当代的世界,就像幻想―个人能跳过自己的年龄、跳过罗得岛一样荒唐。如果他的理论真的超越原来的世界、并建造了一个它应当是的一个理想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就确实存在但只在他的观念里,任何会让你中意的东西都会成为感情的成分。变更是很难的,正如所引的谚语说的:“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在作为自我意识的理性和作为现实在握的理性之间,把前者和后者分开,并防止前者满足于后者的是一些抽象的桎梏,一些这样或那样未经解放就进入概念的东西。把理性当做以十字形交叉为形式的互赠礼品的玫瑰,并因此去享受这个礼物,这就是理性的洞见,它使我们和哲学给我们提供的实际的和谐重新言和。 马克思作了小的但很关键的改变,即从作为名词的“跳跃”到作为祈使语的“跳跃”。和恩格斯的话不同,这是一句没有讲出来的话。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是这句希腊语的字面翻译——被马克思改为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通过紧接下来的对黑格尔的重复改造,他把对理性的神秘接受就仿佛十字路口的一朵玫瑰花这一信息改变了,于是允许我们享受这个礼物,并能对抽象的奴役状态那样看见所有的变化。他把它改造成了一个变化的信息,对伊索式挑战的更富有生命力的接受。 在思考布巴内斯瓦丽·芭杜丽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现在我似乎已经把我的女祖先怪异的自杀插入了理论的理性和革命的紧迫任务之间的缝隙里。我感到我的任务就是用马克思的全部观念来描述她。但是,这个姿态和任务还不能形成对集体性和公共领域的思考。 事实上这正是那篇文章开始的地方。不是把底层人作为一种差异状态来理解,从而开始我对底层人的研究,而是在这里打造一个可能的基础,以便不让底层人把底层状态作为正常状态来接受。我把布巴内斯瓦丽设想为革命的主体(如它本身所是),这本身就质疑了撒替的前提,但却不能得到承认。她还是那样非凡。因此我当时不能从她身上得出什么结论。不过我当然绝对没有把撒替说成是反殖民主义的抵抗。我想到了撒替的罪孽性质,但它却曾是一件不被怀疑的好事,还没有和妇女的主体―形式相联系。殖民地的教育保留了阶级的内在性,我曾试图努力地去理解,那些妇女,也许在我之后的两三代人,依我自己的推断,为什么还会以传统的意义来考虑撒替。如果认为我会支持撒替,那就是幼稚可笑的,但是,我需要从自身走出来。 年,芮玻·康瓦尔把撒替习俗付诸实践,她的母亲微笑了,我当时预料到了这个微笑,那是我阅读《达摩经》时所理解的文本。这个微笑对经文点头称“是”。那个愿望不得不被重新安排,我感觉布巴内斯瓦丽重新安排了那个愿望,是在情景的祈使语气的胁迫下进行的。 她还教了我另外一课:死亡正如文本。她使我了解到没有引起反应的那些情景,如果和平的过程没有可靠性,如果整个国家被变成一个装上大门的社区,青年人尚不知如何珍惜生命——布巴内斯瓦丽只有17岁——你可能会感到当你和我为了相同的原因而死时,有必要作一个答复。肉身炸弹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性,其自身愿望被重新安排了的一种集体性。死的决定和布巴内斯瓦丽事件中的差不多。正是第二个决定的发生推迟了她特有的死。这种观念——当你和我为同一原因而死,由于你不听我的话,由于我不能和你说话,但我们的确为了同一个愿望——属于极端的行为。那些经文能在多大程度上给愿望以公断?这个问题既属《古兰经》,也属《达摩经》。 “底层人能说话吗?”这一研究对我来尚未结束。一方面,是在学校的工作。另一方面寻求,一个非宗教主义作为社会公正的法律工具,使其接纳底层人,这是一种正在消费的利益,只在这里提一下。 暴风骤雨更猛烈些!投稿荐稿请联系:bfzygzh.白癜风有什么症状北京白癜风治疗用什么方法好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eiguihuaa.com/mghxx/1421.html
- 上一篇文章: 2017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教育教学知识
- 下一篇文章: 一家之言视信教为大逆不道是一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