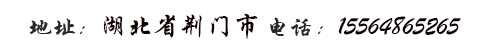时代建筑2016年第3期主题文章江嘉玮陈
|
超越东西南北——当代建筑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李翔宁、邓圆也探讨了当代建筑评论的三个向度,提出当代建筑评论也需构建具有特殊性和地方性的知识系统。曼努埃尔·夸德拉回顾了文化演进中几个不同时期的城市场景,这几个场景恰好反映了人的境况、城市建筑、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历史进程中的传承和变异。卢永毅撰文考察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现代建筑在近代上海的传播,呈现其在被接受和转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性。阿克塞尔·索瓦撰文通过三个案例分析说明,作为技术手段,建筑与城市设计如何参与调解建筑与城市化之间的矛盾。周榕论述了中国建筑师的三个亭子设计及其对应的三种不同的文化观念、设计思考和处理方式,并对中国语境中的“建构”理论进行了反思。森古·奥依门·古尔介绍了土耳其博德鲁姆的德米尔别墅群设计,展现了建筑师图肯特·坎瑟沃如何通过建筑语言来表达自然与文化的共生。露斯·沃得·采恩撰文分析了“罗杰里奥·萨尔莫纳拉美建筑奖:开放空间/集体空间”的宗旨和获奖作品,强调塑造公共空间是解决拉丁美洲复杂城市问题的良药。刘晨以没有灵魂的缪斯和被驯化的金字塔这两个比喻分别指向西方化对中国城市文化的影响与博物馆建设潮现象。江嘉玮、陈迪佳通过对“模型”与“类型”在建筑理论和设计中的演变,展现相关意大利学者对城市建筑的历史分析,并反思两者对当代建筑学研究的价值。田唯佳、宋玮撰文分析了环地中海建筑的地域性特征。 本期主题文章 [1]李翔宁,邓圆也.建筑评论的向度:当代建筑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J].时代建筑,(3):6-9. [][秘]曼努埃尔·夸德拉.认同——人之境况的建筑:由五个篇章和一个尾声构成的思考[J].莫万莉,译.吴彦,校.时代建筑,(3):10-15. [3]卢永毅.实践与想象:西方现代建筑在近代上海的早期引介与影响[J].时代建筑,(3):16-3. [4][德]阿克塞尔·索瓦.建筑及其调解的力量[J].陈迪佳,译.邓圆也,校.时代建筑,(3):4-8. [5][土耳其]森古·奥依门·古尔.自然和文化的共生:土耳其博德鲁姆德米尔别墅群[J].高长军,译.周梦莹,校.时代建筑,(3):9-33. [6]周榕.三亭:建构迷思与弱建构、非建构、反建构的诗意建造[J].时代建筑,(3):34-41. [7][巴西]露斯·沃得·采恩.当代拉丁美洲建筑:常识与理想主义[J].伍雨禾,译.张晓春,校.时代建筑,(3):4-45. [8]刘晨.没有灵魂的缪斯和被驯化的金字塔:关于当代中国文化与建筑的两个比喻[J].时代建筑,(3):46-51. [9]江嘉玮,陈迪佳.战后“建筑类型学”的演变及其模糊普遍性[J].时代建筑,(3):5-57. [10]田唯佳,宋玮.内外之间:环地中海建筑的地域性特征[J].时代建筑,(3):58-63. 战后“建筑类型学”的演变及其模糊普遍性 TheEvolutionofPost-war“ArchitecturalTypology”andaVagueGenerality 江嘉玮陈迪佳JIANGJiawei,CHENDijia 0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北部,以卡洛·阿尔干(GiulioCarloArgan)、穆拉托里(SaverioMuratori)、艾莫尼诺(CarloAymonino)、格里高蒂(VittorioGregotti)、阿尔多·罗西(AldoRossi)等为代表的学者圈将类型学发展为一类进行城市建筑调研与设计的方法,并借此表达城市历史研究的立场。他们对类型的理解各有差别,但共同点是,“类型”概念或多或少带有理想化的特征。这一种类型学思考指向建筑的本质问题,本文将就此展开回溯研究。 讨论建筑类型学与城市形态学的意大利圈子主要成员 1模型与类型:从德昆西到阿尔干 19世纪上半叶,卡特梅尔·德昆西(QuatremèredeQuincy)出版了两部辞典:《方法论辞典》与《建筑学历史辞典》。两部辞典均收录了“类型”(type)词条。关于这一词条,德昆西首先写道,“‘类型’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词语‘typos’。根据普遍的用法,这个词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所具有的一些差异。它基本覆盖了‘模型’、‘模具’、‘印章’、‘范’、‘浅浮雕’等词里面的大部分含义。” 从古希腊词源来看,“模型”与“类型”之间的关系比较笼统,相互涵盖。即使在德昆西所处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语情境中,“type”这个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普遍地被当作“类型”来使用,相比之下,更常见的词是“genre”(种类)。当一门语言处于转型期,新的定义通常会包裹之前的语言习惯出现,并且被注入更新后的理解。德昆西紧接着描述了“模型”与“类型”的区别,“比起‘模型’,‘类型’这个词没有那么多地呈现出可供拷贝或彻底模仿的物像,而更多的是有关各个要素的思想,这种思想本身就应该作为模型里的法则。‘模型’则被理解为与艺术作品的实际操作相关,它是一类可被重复的物体。‘类型’与不同人对艺术品的创作方式有关,这些艺术品无相似之处。‘模型’中的一切都是精准的、确定的,而‘类型’中的一切却多少有点模糊。” 德昆西的《建筑学历史辞典》的意大利文译本出版于年,之后,“类型”这个概念一直都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讨论。直到年,意大利艺术史学家卡洛·阿尔干才根据德昆西的词条做出了新的解释。他在《论建筑类型学》中,将建筑学中的类型学与具象艺术(figurativeart)中的圣像学(Iconography)做了类比。他认为从操作层面上看,建筑设计与艺术创作是平行的。在德昆西的理论基础上,阿尔干进一步提出,“类型”应当被理解为形式的内在结构,或者是某种原则,它包含了无限种可能的形式变体(formalvariation)以及对“类型”自身更进一步的结构调整。与德昆西不同的是,阿尔干提到了“类型”的形式变体,他认为“类型”是后验的(aposteriori):“类型”的这种模糊性(vaghezza)或普遍性(genericità),使其不能直接作用于建筑设计或形式操作,这也解释了一种“类型”是如何形成的。“类型”从来不会先验地出现,而总是从一系列的案例中演绎而来。因此“类型”的诞生依赖于一系列建筑的存在,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形式与功能上的可类比性。 据此,拉斐尔·莫内欧(RafaelMoneo)明确指出阿尔干排斥了德昆西的“类型”概念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成分。这是阿尔干在德昆西的“类型”概念的基础上所做的最突出的改进和贡献。德昆西谈的是理念化的基本原则,阿尔干则开始偏向于类型学在历史与设计中的应用,而非仅限于理论方面。德昆西认为“类型”虽然存在但模糊不清,它不是一种确定的形式,而是一种图式(schema)或是形式概要(outlineofform)。阿尔干认同这一点,但进而补充,“类型”总是从历史经验演绎而来的。通过“演绎”(deduction)而不是“归纳”(induction),阿尔干尝试探寻“类型”的模糊性与普遍性如何存在于众多历史个案中。对他来说,“类型”不仅仅是理念上的原则,还必须带有实体化的一面。阿尔干对“类型”的重新定义削弱了这一概念在德昆西理论中的形而上学色彩,此后的学者也将这一点成功转化为建筑设计中的方法,并应用到城市的历史研究中来。 0世纪60年代的“建筑类型”研究:穆拉托里、艾莫尼诺与罗西 二战后,以穆拉托里为首的学者在展开历史城区调研的过程中,开始建立所谓的城市形态学理论。城市形态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包括广泛的社会调研。穆拉托里将“类型”看作一种形式结构,它反映不同规模的城市里存在内在的连续性。尽管穆拉托里认同“类型”具有理想化的一面,但他并没有将“类型”看作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倾向于将它看作一种要素,辅助当代人类更好地理解城市是如何生长和扩张的。这种城市形态学的方法通过分析个别要素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城市中的建筑,“类型”主要被用作分析工具。穆拉托里的“类型”理论与阿尔干对“类型”的重新定义并无过多联系。不过,穆拉托里的城市调研方法却在艾莫尼诺与罗西那里得到了延续。 3—5年,罗西接受艾莫尼诺的邀请,作为助理教授参与其在威尼斯建筑大学的“建筑的组织特征”(Caratteridistributividegliedifici)课程,并将讲义结集出版。艾莫尼诺与罗西通过这些文本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建筑类型”(tipoedifiliza)的概念。 在《一种建筑类型学的现代观念的形成》中,艾莫尼诺的分析清晰地指向诞生了现代布尔乔亚社会的城市环境,涉及新兴的中产阶级以及启蒙建筑师的乌托邦设计。他将“类型”的概念看作在城市环境及使用功能之外寻找建筑最根本特征的途径。 艾莫尼诺说过,“建筑类型学不存在唯一的定义;它是一门工具,不是分类。”艾莫尼诺与罗西都拒绝将类型学看作简单的分类问题,不希望类型学的内在维度被简单的或者是单一的分类标准所掩盖。 在《城市建筑学》中,罗西认为一切对城市建筑的历史研究都无法绕开类型学。一种特定的“类型”和形式与生活方式有关,尽管它的具体形态在不同的社会里各不相同。罗西将“类型”这个概念看成是永久与复合的,是一种先于形式的逻辑原则。“类型”伴随着城市建筑的形式自主性,反映了建筑作为一种存在的很多状态。罗西认为它最接近于建筑的本质。 相对于阿尔干及艾莫尼诺的“类型”概念,罗西强化了“类型”自身凝聚的城市集体记忆,明确指出类型学上的创新是不可能的。罗西的“类型”概念以类似于历史范例的方式出现,它的模糊普遍性(vaguegenerality)在于这个具体的历史范例如何能够适配到具体的城市情境中。这种模糊普遍性既指历史范型的普遍适用原则,也指历史范型在使用过程中不需要被精确地重复,于是模糊普遍性可被概括为“类型”的典型特征。此外,罗西的“类型”概念还将自主性引入建筑学,这超越了“幼稚的功能主义”(naivefunctionalism)。他的类型学表现出一种带有历史关怀的研究与设计立场,反对那种在意识形态下漠视城市既存环境的态度。 3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类型”、理想形式与历史视角 根据从德昆西、阿尔干到艾莫尼诺、罗西的观点,笔者认为,“类型”有四类存在状态:(1)理念,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一种集体理性,从个人的角度看它又可以是艺术家、建筑师的创作;()文字,通过概念指涉来描述内在的控制原则,尽管这种指涉存在局限性;(3)图纸、模型或一切表征建筑的媒介,这意味着将理念实体化;(4)实体建筑物或城市建成环境,被漫长的历史筛选、浓缩与凝固。对于在城市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公共建筑,我们需要以“类型”的方式将其呈现为理想的形式,否则应当摈弃;大量重复出现的城市建筑,比如住宅,则无需以公共建筑般的“类型”来规范。形式作为独立于功能、社会关系的要素,理所当然成为表征“类型”理想化特征的一种途径。 我们可以按照这类思路列举一些历史上的经典“类型”:希腊帕提农神庙和罗马万神庙、伯鲁乃列斯基的穹顶、罗马的斗兽场;圆厅别墅;19世纪末开始出现在城市郊区的独立住宅。区分“类型”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状态,有利于辨明“类型”的变体所包含的历史信息。 我们通过具体案例来考察一些经典的“类型”与理想形式、历史语境的关系。哥特大教堂的例子可以佐证“类型”如何出现在共时性的变体中。维欧莱-勒-杜克提出的“理想大教堂”(lacathédraleidéale)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系列在同一时期、相邻区域建造出来的哥特大教堂的集合。巴黎、亚眠、兰斯、博韦、苏瓦松和努瓦永这些城市在兴建主教座堂的时候都有类似的社会背景、建造团队以及委托方式。这些共同点足以支撑每一个大教堂变体呈现出理想“类型”的吉光片羽。可以说,维欧莱-勒-杜克的理想大教堂是一种被归纳出来的“类型化”实体。一些普遍性的特征转化为具体的形式语汇嵌入每一个个案,比如西立面的钟塔、中殿的尖拱、玫瑰花窗的纹样等。这些哥特大教堂的剖面轴测并排放在一起,呈现出“类型”的模糊普遍性的共时状态。 哥特大教堂的理想类型 “坦比哀多”的原型以及类型演绎 “类型”的历时性维度比共时性遭遇更多历史突变,正是这些历史突变检验了“类型”的理想形式。先例(precedence)对于历时性的“类型”演变来说很重要,它对于后世变体的意义就像一副柔性的石膏反模,每浇筑完一尊雕塑,都可以调整形态再去浇筑下一尊。这副反模的内轮廓好比是形式,只有当这些形式上升为“类型”,被它投射出的实体才具有无限的价值。伯拉孟特(Bramante)设计的“坦比哀多”(Tempietto)以及它的先例与后世演绎就是一个形象的案例。“坦比哀多”具有的若干形式特征,显然依赖一个“类型”——维特鲁威在《十书》里描述的环柱廊圆形神殿。这座神殿通过某个具体的历史“模型”将进行“类型化”的抽象整合,从而使自身同时呈现为“模型”与“类型”。后世的这些“坦比哀多”变体,体现出一种模糊普遍性在历时维度上对先例的调整,适配具体的历史语境。 4模糊普遍性与“类比”方法 罗西在发展了成熟的“建筑类型”概念之后,开始在0世纪60年代后期使用类比的方法(analogy)来研究建筑在城市环境中的模糊普遍性,并且尝试将历史转化为设计。他借鉴了荣格(CarlJung)的“类比”思想。 之后,罗西发展出“类比建筑”与“类比城市”的概念。在《城市建筑学》中,罗西曾引用18世纪意大利画家卡纳雷多(GiovanniAntonioCanaletto)的画,画中的逼真场景拼接自帕拉弟奥的威尼斯里阿尔托桥方案、维琴察的巴西利卡以及基耶里卡蒂宫。这是一幅想象出来的威尼斯城市景观,三座建筑全是帕拉弟奥的理想类型,它们都不在威尼斯,却被共时地拼贴到一个地方,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语境。 卡纳雷多的油画《卡布里奇奥》 罗西从卡纳雷多的画里借鉴了“类比城市”的手段——寻找作为“类型”的建筑实例,依靠城市场景的拼贴,创造新的城市历史情境。在年的“米兰三年展”上,罗西的长幅作品《类比城市》(cittàanaloga)呈现了众多经典的建筑,它们都按照为人熟知的经典角度呈现出来,整幅图面都是以建筑作为主要元素进行的历史情境的拼贴。这种带有模糊普遍性的类型学视角,使罗西的类型学转化常常呈现为历史或是形式的片段,讲求可被移植的形式与空间氛围。 《类比城市》 从阿尔干到罗西,“类型”的这种模糊特征给艺术家或建筑师的创作带来了更广阔的历史援引。这种模糊的普遍性让艺术家或建筑师重复“类型”的创作过程,而不是直接复制“类型”。当类型学被罗西等人沿用到城市问题中,它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历史研究,而是试图成为一种设计工具。然而,或如荣格所言,“类比”行为本不该转化出实体,因而罗西借此谈论的建筑自主性问题,很可能在理想形式转译历史片段的过程中显得独断和专横。 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意大利建筑类型学与形态学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随着塔夫里、罗西受邀到美国访学,建筑类型学进入美国。年,意大利《美丽家居》(Casabella)杂志以“类型学的根基”(Iterrenidellatipologia)为主题出版了一期专刊,对过去近0年的建筑类型学做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讨论。其中,罗西在采访中被问道,“我们都知道您是类型学和城市研究的重要发起人,现在您为何不继续进行这些研究了?”我们不妨以罗西的回答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跟我的同事最初的研究是想让建筑学的学科框架更清晰,为年轻建筑师提供更多的自由。不过,要是将类型-形态学研究当作建筑学的主流,这很可能反过来又约束了这种自由。功能主义曾经给它自己制造出很多神话,我不希望看到类型-形态学重蹈覆辙。” (感谢安东尼·维德勒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指点。) (图片来源:图1,作者自制,源素材来自网络;图,作者根据舒瓦西(AugusteChoisy)与维欧莱-勒-杜克的图解重绘;图3,作者重绘;图4,图5,来自网络)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作者简介:江嘉玮,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耶鲁大学访问研究助理;陈迪佳,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eiguihuaa.com/mghjz/1449.html
- 上一篇文章: 健康最大的克星是湿气,老中医私藏祛湿
- 下一篇文章: 300多年前,老祖宗就留下了的这套长寿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