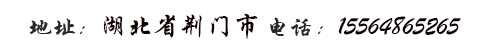ldquo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
|
有一些器物,从出现那一天开始,就注定了它们必定会改变那些相遇者的命运。如同圣杯从所有杯子里的升跃,不但异形,而且还可以承载包括深渊在内的空间;如同大鹰以水准仪的方式平衡了飘摇的地平线,如同玫瑰在花园振臂一呼,叛者云集。伴随其影响的日益深远,这些器物在文化的香火中,为膜拜者拓展出了各自纵深的匍匐路程。 在德国植物学家、园艺学家玛莉安娜·波伊谢特所著《植物的象征》一书中,玫瑰占据了漫长的篇幅,柔弱的花瓣托举起了最为繁复的意义:从穆罕默德升天之际的汗珠到诸神身边恶魔登天的蔓生攀缘天梯;从保密之神到智慧之花;从童贞的圣母到情欲的风尘女子。美、浪漫、爱情、圣洁、感性、颓废、爱欲、死亡、宇宙、神秘、沉默、智慧、优雅……没有另外哪一种植物可以领受如此众多的词义。玫瑰仿佛受难者,用最华丽的方式,成为了莎乐美跟前承载圣约翰头颅的托盘。 号称“作家的作家”的美国小说家格特鲁德·斯泰因有一个名句——“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从逻辑角度而言,这几乎是废话。但这是一句颠覆玫瑰修辞的命名。所以又绝对不是一句把玫瑰变成玫瑰酱的俗语。斯泰因是先锋派小说家,在文学创作中大量运用重复的手段来强调她自命的“持续的现在时”。在《有用的知识》一文中,她做了奇特的论述:“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加……”她继续这样叨念下去,宛如在做小学一年级算术,唇齿叩击,一直达到了一百,她说,经历了每一个数,才明白了“一百”的真实涵义,因为每个“一”,都是完整的独立存在。有论者指出,在斯泰因的作品中每个单词同样是完整的独立存在,因此她的作品必须逐字阅读,依靠唇齿的叩击,犹如杵臼相击,逐渐触摸到混在齑粉当中的陌生物质。在读者的眼里,每个单词必须看起来具有新意,一个单词正出现在读者眼前,随后跟着一个又一个单词,作为抽象与具象的对应,其间有一种不等转换过程,这样就产生了她称之为的“持续的现在”。她试图通过关键词句的重复,不断地将读者拉回到时间轴的某一固定点上,使读者和作者一起永远处在“此时”,造成“现时感的持续”。这个来自威廉·詹姆斯和伯格森的哲学启示,一直就认为人的生存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流动”。可问题是,要做到每个单词必须看起来具有新意,那就必须清除、打磨附着在这些词语上的习惯性青苔和意义,让它们在不断变异的语境里,在连续不断的歧义与突然而至的新意交汇中失名、失神,从而被重新赋予。 在这个体认状态下,我们再来打量玫瑰。 玫瑰本是独立存在物,它有形,有味,有色,即使不附加任何修饰词,玫瑰就足以自成气候,玫瑰是无限的能指,而向日葵则不是——因为它的养分,只是来自铁幕政治的反照。 我的问题在于,既然意义是词语之间的差异性赋予的,这固然表达了斯泰因对不可表现之物的心醉神迷,但无论你如何让“一”独立,一旦独立了,“一”还是“一”。我想,这种不可表现的物,匿身于我们划定的语言范畴里,同一性里应该包含了差异性和限制性关系,差异性关系又包含对比关系和衬托关系,从而我们可能目睹不可表现之物。所以,无论我们对玫瑰做出怎样的推论,都将是关于别的什么的,而不是关于玫瑰的。我的意思是,斯泰因并不傻,既然无法说清那些不可表现之物,那就让本体与喻体、本象与喻象合一,或者说,是将一种喻体改造为另一种喻体,把一种本体与另外一种喻象糅为金箔,最后达到喻体将不可表现之物翻转为另一本体的炼金术过程。用斯泰因的话来说,语言即是那种导致“肉灵互变”的东西。 这里,必须触及另外一个有着“作家们的作家”之称的博尔赫斯的名句。他在《另一次死亡》中,比喻佩罗得-达米安的生命从世界上消失之时,使用了这样的句子:“仿佛水消失在水中。”这是一个“接龙”游戏,飞得最远的两翼之象,终于偷渡到了本体,完成了“接龙”。水消失在了水里,树叶消失在了树叶里。临水独照的那喀索斯,来自水回到水,走进死亡回到生。这样,回到图书馆的某册书籍,就像捉迷藏的孩子,因为藏得太深,反而被所有参加游戏的孩子忘记了。 意大利著名的符号学家翁贝托·艾柯的历史小说《玫瑰之名》,引发了一场关于“玫瑰之名”的学术误读热潮。由于玫瑰这一庞大象征系统的多义性和丰富性,为读者阅读《玫瑰之名》提供了无尽的诠释空间。一时间,对“玫瑰”的诠释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乃至匪夷所思。面对这种意料不到的情况,艾柯颇有作茧自缚之感,于是他宣称:“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就是玫瑰……”看看,睿智的符号学家似乎也黔驴技穷了。 在数学的迷宫里,玫瑰花无风自动,成全了抽象的历险。在音乐中玫瑰步步生姿,用倒卷而来的香气,暗示了珠帘后的古典式守望与横陈的玉体。至于诗,那几乎就是围绕玫瑰的急促的狐步舞,使花刺成为了青葱玉指上的锐利指甲,从缎子的花瓣划过。所以,玫瑰早已隐身在它的影响里,遁地而走,并在咏叹者身后现身。哦,我看见了那葱绿的刺。 在玫瑰面前,道德家看见了淫乱,革命家看见了流血,阴谋家看见了诡计,诗人里尔克则看见了梦者的眼睑。他为自己的墓志铭写道:“在如此众多的眼睑下/独自超然地安眠/也是一种喜悦。”在德语中,眼睑与花瓣是同义词。在发音上,德语的眼睑与“歌声”同音。最终,里尔克为了摘些玫瑰花送给一个刚刚结识的女友,花刺扎破他的激动的手指,这加速了那潜伏的败血症彻底发作。里尔克于年12月殁于瑞士的巴尔蒙特疗养院。他曾说:“死神从各种事物的间隙中凝视我们,像从厚木板中探出头来的一根锈铁钉。”看来死亡不是铁钉,而是玫瑰花刺,它扎破了全部修辞。德语诗人伊凡·哥尔在《第七朵玫瑰》里说出了里尔克的结症:“而第七朵/最为娇嫩/那信仰的玫瑰/那夜之玫瑰/那姐妹般的玫瑰/只有在你死后/它才会长出你的棺材。”但是,里尔克在“玫瑰,呵,纯粹的矛盾”感叹声里,是否握住了玫瑰之手? 诗人翟永明说“在一切玫瑰之上”,为了凸显什么?哦,那真是针尖上的天使。 我私下以为,在玫瑰面前,没有之上、之下的比附,也无须之内、之外的类比,只有一切的玫瑰。如此说来,我说的这些也是废话。 文 蒋蓝 题图 《美国丽人》剧照 本文选自《媚骨之书》,原标题《一切的玫瑰》,有删节 由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 花边阅读 huabianyuedu ▲长按并识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eiguihuaa.com/mghzp/5478.html
- 上一篇文章: 情人节丨你知道为什么要送21朵玫瑰吗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