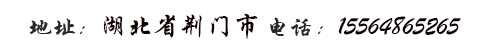心中的玫瑰花第二篇ldquo迟拍
|
作者:齐振英 心中的玫瑰花 第二篇“迟拍”的照片看着面前的几张照片,它拍摄于年1月。那天,晴空万里,我们一行四人,从省城出发,去曾工作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工厂,参加一个座谈会。在会议间隙,时任厂长李献洲陪我到我原来工作过的地方,看了看,留下了这几张照片。它把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二十世纪的年12月--年4月。啊,已经四十多年了。 之所以本文叫“迟拍”的照片,就是因为当时,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未能留下一张照片,以至于在40年后,才有机会拍了下来。所以说,这几张照片就是“迟拍”的照片。 回忆就是重逢。通过这几张照片,亦能使老工友们在一篇文章中相聚,蓦然回首瞬间,往事匆匆飞跃,昨日种种,恍然如梦。亦能使在一篇文章中,在不经意间,许多人和事,又浮出了水面。那些模糊的面孔,那些远去的背影,已不知去何处找寻?在这里,他被找到;亦能通过美好的记忆,加强联系,多沟通,多见面,其也是一件乐事。有回味,有意义,有展望。 01 大摇臂钻床旁 迫不及待地进入””分箱,来到我曾经工作过的位置,一眼就看见这台大摇臂立式钻床了。即大摇臂立式钻床。它是沈阳中捷友谊机床厂出品的。可能是我厂最大的立式摇臂钻床了。看见它,我好吃惊,产品质量就是好。 它在“”分箱西南角的位置。我年12月知青招工进厂后,经过三个多月的集训队培训后,就分配到对外番号是“”分箱工作,进而分配到模具组,叫模具钳工。主要工作是做锻造模具、铸造模具、钣金模具和冲压模具。我年12月知青招工进厂后,经过三个多月的集训队培训后,就分配到对外番号是“”分箱工作,进而分配到模具组,叫模具钳工。主要工作是做锻造模具、铸造模具、钣金模具和冲压模具。 说到大摇臂钻,我身后的这台,印象太深了,这是我40年前曾操作过的设备。学徒的前半年,都没有敢动过它。半年以后,才开始操作它了。 模具,素有“工业之母”的称号。它是在外力作用下,使坯料成为有特定形状和尺寸的制件的工具,被广泛用于冲裁、模锻、冷镦、挤压。 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正在和师傅一起操作这台摇臂钻;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正一手拿着吊车按钮,一边扶着大模块模具,正在往钻床台子上慢慢地放;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正在加夜班,“分箱”里灯光不是太亮,睁大眼睛,突击干活。 兵工厂的性质,决定着我们的模具特别大。模具组,干得是“”分箱“四最”的活。即:最重的活,最脏的活,最累的活,最大的活。做这些活,离不开大摇臂钻床、小钻床等。我在这个摇臂钻床前工作了两年整。最重的活是干“主动轮”的铸铁沙箱。这个铸铁沙箱特别大,体积相当于重型卡车的一个轮子那样大小,要在上下两个箱子的两个端面,钻四个孔。干立体砂箱的任务很重,一两个月总要来那么一批,大约有二三十个吧,摞起来,占得地方很大,也很高。 干活的程序是:先用吊车吊起来,放到划线台,请画线的马文素师傅,马凤玲师妹来画线,划线划完后,再用吊车吊起来,吊到钻床旁,再用吊车,把它吊到钻床的台面上,这是很麻烦的。在砂箱的两个端面,钻两个孔,凹凸两个砂箱,钻四个孔。干这种活很脏,因为是铸铁件,上面附带着残余的黑沙子特别多。有时,吊车砂箱一吊起来,黑沙子呼呼地往下掉,弄的我们浑身上下黑乎乎的,干这种活,也容易出事故。因为砂箱个头大,另外,还是铸造铁件,许多地方不结实。有时候,还会掉下一大块铸铁,搞不好就砸住人了。这种活来得急,要求速战速决。为此,经常加班加点。我和王秉武师傅,经常干这样的活。这样的活,好像在模具组属于最累最脏的活,因为王秉武师傅是班长,事事都要起带头作用。工作虽累,但我年轻力壮,全然不顾。 有一天,我正在干活,教导员底君领来两个人。经介绍得知,是我父亲铁路某单位派来的人,这两个人告诉我:“我们今天来,是专门征求意见来的,是有一件重要事情告诉你,你的父亲,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被错误的定为‘走资派’。你们全家受到委屈了,现在,组织上已决定给予平反,你父亲已经回家了。今后,你父亲的问题,再也不会连累你们子女了。你们子女上学、参军、提干等,都没有问题了。你们家属,有啥要求?”我心里想:“有啥要求,我父亲,八年了,被你们看管着,连回家的权力都不给,身心受到严重迫害。我们作为子女,在上学、参军等,受到影响,都已经失去四五次机会了。”听到这里,我的泪瞬间淌了下来,这是痛苦的泪。 当时,年,国家恢复高考刚刚结束,这是第一次高考,我都没有敢报名,就是因为父亲当时没有平反,就是因为担心政审不过关。实际上,年恢复高考时,政审还是比较严格的,许多达到分数线上的考生,由于其政审不合格而被刷掉了。 在摇臂钻床的右后面,厂房的外面。有二间房子,是“”分箱的计划组和机电维修组。计划组有一个胖点的师傅是组长,四十岁左右,名字叫陈长礼,有一次,医院住院,“分箱”派我去照顾他半个月,他们同组的还有张金贵、候景玉、魏振国师傅。机电维修组的师傅有:薛双利、李庆和、周##、耿建国、李振河。干活时,在我们的背后,是一条“分箱”的工作通道,从“分箱”的东头一直贯穿到西头,人们走来走去。 再往东,是一台大型龙门立式铇床,是一起进厂的张国华兄操作的,他和铇工班班长刘俊学一起操作。刘俊学约四十多岁。顺着通道,再往东走,就是刀具组。刀具组在“分箱”的东北方向,这个组人最多,他们是两班倒,在小房子里面干活。 刀具组的师傅及工友有:郑林津、王天佑、程福贵、周桃英、赵淑青、井海顺、孟祥云、蒋运芳、许铎、何建新、王步雷、聂素霞、范堂保、赵会芹、张风琴、何小英、王旭世、王洪生、王林明、吳兰英、郭強、李春兰、宋~~、李亚兰、陈会珍等。 郑林津师傅,是原京字九五二部队的就地转业战士。他的老家是浙江临安市,是人杰地灵的地方,有天目山、青山湖、钱王陵、玲珑山、太湖源、浙西大峡谷等。临安有真山、真水、真空气,是距沪、宁、杭大都市群落,是生态示范市。我曾去过两次,是参加会议,尽管来去匆匆,但真的是少有的好地方。我只想在马路上和郑师傅能偶尔碰上,那才多高兴啊。 再往东走,走到头,就是量具组。量具组的师傅及工友有:国昆昌、董久昌、胡铁鹏、魏礼正、常芗熹、董重兵、董兴荣、吳素辉、王宝良、韩素珍、运河叶、刘京英、何新国、庞艳秋、徐秀英、张秀琴、董其武。 其中,董其武师傅,个头不高,较胖,福建人,40多岁,他和郑林津,都是建厂元老,原京字九五二部队的就地整建制转业的战士。在27号单身宿舍楼,和我住对门,他的屋里干净极了,一尘不染。他是我见过收拾屋子,收拾得最干净的人。他还经常到我们的房间,指导我们搞卫生,一生受益匪浅。 其中,量具组的运河叶,一位十七八岁的女孩,是当地部队干部子女,记得,有一次,刚参加工作不久,在一次下班后“分箱”组织学习时,她笑着对大家说:“我刚来到工厂,许多事特令我骄傲,比如说,三线工厂对外保密。建厂时,老一辈人就想到了。进入太行山区,找我们这家兵工厂特难,它建在了这么深的山沟里,离公路还很远。”她接着说:“我曾在语文课本上学过陶渊明的一首诗,叫《桃花源记》,诗中这样写道:“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首名作,所描写的“豁然开朗”,形容在山沟里我们的工厂,非常适合。你看,我们工厂,走到一狭口处,才猛然看到神秘工厂的大门口,隐秘性特别强。” 钻床的西侧,是我们组王建民、邱雅丽的电火花机床。再往西,是我们组划线的马文素、朱小冬、马风玲,她们三位的工作台。 接着往西,是下料组,组长焦栓虎,男同志,四十多岁,较胖。还有一个女同志,大高个,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在四十岁左右。 “别人干活,干得都是干干净净的活,怎么轮到我干活,干得却是这么累的活。”有时候,也常常产生这样的思想问题,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思想问题”了。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就是要过思想这一关,这是解决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的问题。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是年轻人,干活还能累死?再说了,师傅们能干,我们咋就不能干!”就这样,没觉得苦与累。古语云,“欲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思想关,就这样过了。是啊,对一个人来说,把好思想这一关,真是一辈子的事情。 02 干最脏的活 上图我站的位置,就是我干最脏的活的地方。我曾蹲在那里干“抛光”活。模具组最脏的两件活,一个是打大砂箱的孔,就是在大立式摇臂钻床上打孔,前面我已经说清楚了。所谓“最脏的活”,是相对整个“”分箱而言也。再一个就是模具“抛光”。所谓“抛光”,就是人蹲在地上,用小风砂轮机,在小风砂轮机的机头上,裹着砂布条,然后,在“锻造模具”上的端面上抛光。由于“锻造模具”淬火后,在模具的表层,生成一层很厚的氧化硬铁皮,这需要用砂布抛光来打掉,使它露出白的亮光来。工厂许多人,都见过这种工作环境。他们说:“抛光用的是风动的小风砂轮,转速比小电钻快多了,有各种配套的小磨头,只是操作时太脏了!” 我干这种活的时候,其周围,在四五平方米之内,砂布沫子满天飞,砂粒满天飞。砂尘、布条灰尘滚滚。场景就像沙尘暴,又像龙卷风。一干就是好几天,干完这种活以后,连续几天都不想吃饭。鼻眼儿里、牙缝里、口腔里,到处都是砂布沫子、砂粒沫子。干完这种活以后,好像得了一场大病一样,这种活,每个月都要干上七八天。 所有这些,我从不计较,我一边学习,一边干活,在那个年代里,也许是年轻、也许是兴趣,虽然脏和累,也并不觉得什么。我想这就是农村知青生活,给我们的历练吧,也是知青阅历,为我们那一代人所创造的财富吧。说真心话,从来没有计较过苦和累。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起当知青,一起进厂,一起进同一个“分箱”当学徒工的党勇志同志,还记得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看见齐振英干这种活时,浑身上下捂的严严实实的,尽管那样,摘下口罩后,满脸还都是黑乎乎的。” 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正蹲在脚底下那块地方,手拿缠有砂布条的风动电钻,戴着口罩,戴着帽子,浑身捂得严严的,干抛光的活。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干活周围的许多人,一看到我在抛光,都捂着鼻子,远远地跑开,远远地离开这个“沙尘暴”。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在这里忙来忙去的身影。这里有汗水,有辛苦,可看到抛光干净,表面露出“白光”的“锻模”时,我的心里有欣喜,有快乐,心里充满了完成任务后的胜利自豪。 03 模具组 上面这张照片,是我曾经工作过的模具组的位置,我和师傅的工作台,就在我身后的位置。整个厂房格局未变,“”分箱的格局亦未变。后来,听说,模具组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工厂不做模具了,这个组给解散了。 接着说,从兵工厂办公楼后边往厂区走,进“分箱”的东门,依次路过铣工组、磨工组,龙门铇床,就到了模具组。四十年前,各位师傅的工作钳台的位置,现在已荡然无存了。但身后的玻璃窗、地面等,都未变。我在这里是恍惚,是做梦,不知道。 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的身后各位师傅正在忙忙碌碌;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正在给各位师傅的喝水杯里倒水;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一手拿着图纸,一手拿着钻头,准备出发到砂轮间去磨钻头。 记忆中,师傅们的钳台,在我脚站的位置依次排开。从左到右依次是:张树亭,26岁,年入厂,年和钣金“分箱”的女工李小明结婚。李振卿,河北深县人,40岁左右,机械中专生,爱人是农村教师,后来连同子女一起解决“农转非”。米新民,30岁左右,机械学校中专生,有两个女儿,爱人在兵工厂家属区服务社工作。王秉武,河北深县人,机械中专生,班长,“分箱”指定的我的师傅,不到40岁,爱人也在家属区商店工作,有二子一女。 冯德全,浙江余姚人,原京字九五二部队战士,是第一批就地集体转业的,他温和、细心、讲卫生。吴志雨,40周岁左右,石家庄鹿泉人,脸色是“运动健将”型。后来调到石家庄手表厂,我调到省直机关后,他多次到我单位联系叙旧,但那阵子,我实在太忙了,或是出差在外地,或是开会,一次也未见到,多好的一位师傅。刘喜芳,他是一名男青年,年入厂,25岁左右,从石家庄入厂,和本“分箱”的车工史风兰谈恋爱,后结为伉俪。冯德全、刘喜芳他俩的工作台挨着,他们两位是师徒关系。 朱晓冬,女,年入厂,大高个,25岁左右,后离开“分箱”,调入兵工厂子弟学校,后在河北医科大学工作。王建民,22岁左右,年入厂,保定“高蠡”暴动革命烈士的孙子,后来,我们一起考入职工大学,同学三年。他的电火花机床,在我们钳工台的对面,电火花机床,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专做模具的一种机床。同一个小组的还有:王洪生、郭树林、吴爱军。邱雅莉刚进厂,是工厂的子弟,跟王建民学徒。我和王书祥、马风玲是一同进厂学徒的。 我即将离开“”分箱时,何瑞南同志从石家庄火车站刚刚调来,他的未婚妻在光学“分箱”工作。听他讲,他是火车站一名调车工,在火车的车辆上,像“铁道游击队”队员一样,跳上跳下,挂钩、摘钩,寒风烈烈,夏日炎炎,吃了不少苦,真不易。我们听了他讲的这一段事情,觉得这名小伙子,身体挺棒。他长得也挺帅。我和王书祥刚学徒两年,没有出徒。所以,不能独立工作,也就没有钳工台。 王秉武、米新民、李振卿,还有后面要提到的,量具组长国昆昌、铣工组张长起等,他们都是班组长,都是-年毕业的老中专生,都在一线当普通工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一点怨言。 在“分箱”走动,我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力量,一种莫名的感动,在这个“分箱”里,曾经发生过很多或忧或喜的故事,还发生过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一段一段让人回味无穷…… 04 卡具组铇工组 上面的照片,在我的身后,是铇工组的位置。我的左后方,我的右后方,分别有两台刨床,都不大。开刨床也好,操作刨床也好,我觉得很清闲。当然,是相比较我们组了。铇床组有:朱成群、陈兵荣、金月新。他们的师傅,四十多岁,叫王庭荣,挺老老实实的一个人。 铇工组还有:王庭荣、张玉亭、李玉山、祖力庭、康宝珍、刘俊学、钱宝君、卢士庄、孙风贤、张国华、刘玉兰。 钱宝君,“分箱”的先进工作者,印象中,她的未婚夫是“分箱”的调度,大高个,不胖,不爱说话,我几乎没怎么见他和别人说过话,不知道他的恋爱是咋谈?。 朱成群是团干部,爱干净,文质彬彬。陈兵荣也是铁路知青,我们一同进厂。铇工组人比较多,他们两班倒。看他们工作,坐在那里,喝着茶水,好舒服啊。 照片左后侧,有一间小房间,是放砂轮机的地方,我经常在那里磨钻头。 铇工组的后边,挨着“分箱”西大门,就是卡具组的位置了。在图片的右前方,是组长刘福和的工作台,他的徒弟是范书正,范书正人很正派,能侃侃善谈。和我们一起进厂。 还有李彪,挺温和的;王志勤,老实人;王自然,男帅哥,长得特白。 卡具组,除去三四位师傅在四十岁左右,其余的都是在二十岁左右,他们干活跑来跑去的,有时还唱着歌,他们组一派生龙活虎的景象。 卡具组师傅还有:毕元胜、吴庆民、陈世芬、高振海、赵兰珍,还有操作座标镗机床的田师傅。 在卡具组的对面是焊工房,有一个男同志,大高个,比较魁梧,叫姚顺和。他的徒弟和我们一起进厂,是个女同志,个子不高,名字叫张素娟,听说当了五年知青,人挺朴实憨厚的。 还有焊工刘玉栋,湖北人,和我同龄,比我早入厂四年,算得上“老资格”的年轻师傅了。我们早晨,坚持锻炼身体练武术,我称他为师兄。焊工组还有:姚顺合、冯效庚。 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正拿着磨好的钻头,从砂轮间走出来;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的师兄范树正,跟着他的师傅刘福和在工作台上忙忙碌碌。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正从前方的大门口,早晨、中午、下午,和工友们一起走进来上班,一起下班走出去。 那时,比较流行的歌曲是:“闪闪的红星”,经常听到范书正、王自然、李彪等,在“分箱”里哼唱,余音至今在我耳旁缭绕。 “红星闪闪放光彩, 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 党的光辉照万代, 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寒, 冬天里,红星闪闪迎春来, 斗争中,红星闪闪指方向,征途上,红星闪闪把路开。 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 05 铣工组和磨工组 上图左侧为车工组崔玉成的立式车床位置,挨着的里面是铣工的位置。其中:中部为工件检验台。 当然,现在都变了。但万变不离其宗。还有许多当年的痕迹。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正在和正定籍的周援朝说着什么,他说的正定味的普通话,特别好听。他是转业战士,中共党员,住单身宿舍,人挺憨厚的。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与师傅王秉武,正在和检验台的马同帮师傅,谈着“锻模”的工艺要求。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我正在和曲领娣,北京人,她好像刚从外地调来,交谈着什么。看到这张照片,我仿佛看到,铣工组的党勇志,大高个,我们同为铁路知青,一同进厂,祖籍又同为老乡,正跟着其师傅,铣工组组长张长起,认真地学习操作技术,他是实干型人才。 王正须,23岁左右,大高个,较瘦,一说话爱笑,爱干净。勤奋型人才。杨国斌,大高个,25岁左右,石家庄籍,不爱说话,头型十分好看。是实干型人才。后来和同班组的王杰美女结为伉俪。 陈克林,天津人,25岁左右,住单身宿舍,经常拿着书,研究磨钻头的角度,看着他那副认真学习的精神,我都有些自愧不如。田培生,25岁左右,大高个,天津人,话不多,憨厚老实…… 铣工组的师傅们还有:王天才、翟贵祥、王蕴苌、贾永田、贾文娟、王秀英、田培生、任伟、任玉敏、王玉珠、杜金娥、王立、耿小明、赵志平、张黑壮、马元才、白风荣、刘文亮。 上图右侧一列是平面磨床的位置。磨工组的师傅有:郭雪岭、齐莉莉、董国顺、罗玉苓、修世堂、李继云、曲领娣、杨丽珍、田学萍、马立新、杨翠茹、时金英、刘双卯、周援朝、蒋建强。 郭雪岭,组长,高个,40岁左右,人挺和蔼。齐莉莉,个不高,说话北京腔,高嗓门,直率型人才。时金英,一同进厂的知青,入厂时是中共党员。 杨丽珍,北京知青,和我入厂时间差不多,好像是高干子女。她是从外地调入兵工厂的。我有幸参加了她的婚礼,在兵工厂招待所二楼的一个阳面房间,吃的她的喜糖。她和丈夫从北京结婚回来,丈夫好像是北京一个兵工研究所的,很帅的。 蒋建强,20岁左右,比我晚一年进厂,石家庄知青,有学识,有修养,爱学习。 这就是我们的“分箱”,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在发生着,在延续着,而我们每个人,就是这些故事的直接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互相帮衬着、磨合着,一起成长,一起走过、续写我们共同的故事。 06 车工组 上图为车工组。在“分箱”的东南方向,有一大片,有十几台车床,型号有大中小。记得崔玉成开的是一台立车车床,就是上图的这台。他爱人(当时是未婚妻),也在这个组。除了组长李建尊以外,其他的同志,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车工组是两班倒,有白班和中班。 班长李建尊,是个大个子,挺威严也挺和蔼。马同帮也是大个子。后来做检验工作,检验极其严格,但也通情达理。 王君祥是与我一起入厂的,井陉县段庄村人。 注重锻炼身体的伙伴们。每天早晨六点钟就起床了,兵工厂的南门外,有一个农民的打麦场。我们就在那里晨练,坚持得很好。每天早晨都来到这里,一块来的,有同“分箱”的詹建平,他是车工组的,还有同“分箱”的焊工刘玉栋,我们跟一个叫高竹亭的师傅学习武术打拳,高竹亭好像是安全技术科的,在兵工厂期间的那几年,我们一直坚持的很好。 车工组的师傅还有:马步增、秘桃来、冷明新、夏露、陈富海、张胜超、曹定国、李亚兰、吴靑霞、尹素风、张贵芳、王君祥、史风兰、丁秀芬、李爱荣、麻胜芝、何建文、李会英、徐尧、姜兰、伍建军、陈惠兰、柳运良、王勇敏、魏素敏、姚喜平、李莉。 照片中通道的顶头,是“”分箱的东门,“”分箱的领导们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办公室仅有一部对外电话,打长途电话时,需要兵工厂总机转出。 “”分箱的领导们:主任王风林,教导员底君,副主任钟孝齐、副教导员陈连堂。 财务室有一个女同志,三十岁左右,较胖,其丈夫在附近当兵,名字好像叫李淑贤。 技术组有两个冯师傅,冯庆潮,后来当过“分箱”主任,还有一个冯世超,大高个,河北深县人。 过去的事情,刻骨铭心,当年,我们踌躇满志,满怀鸿鹄之志,报效祖国,对工作,埋头苦干,忍辱负重,精益求精。 07 爱情 马克思说,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男女双方基于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彼此相互爱慕,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生活伴侣的一种高尚的情感;他还说,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逊甚至羞涩的态度,而决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 马克思是最伟大的哲人,基于爱情这人间最普遍而又最复杂的东西,他早已看清摸透。千百年来,人类进化的可谓越来越完美,文明越来越发达,但爱情这一亘古不变的话题,始终是人们念念不忘、情牵魂绕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不乏爱情的身影,它诉说了多少美好的、真实的、真真切切的故事,它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经典的、美好的、纯真的爱情,至今仍流芳百世。爱情是永恒的主题。 兵工厂的爱情亦是轰轰烈烈,雷声贯耳。该单位地处深山,此地此处就唯此一个单位。青年在这里成家,两条选择,一条是“就地解决”。否则,就在外地找对象,结婚就“分居”。 这段故事,主要是记述70%的青年人,在“就地解决”中所发生的爱情故事。因为此处大山沟,无其他单位。找对象,找爱人,只能在本厂找。这里,没有照片,但脑海中的照片,却总在闪现,不是一张,而是许多张,一张一张地在闪现。 幸福的这些时刻,诸君:是否仍记得! 我们看到:刘喜芳,听着是一位女士名字,实际上是一位帅哥,是一位高个头的帅小伙。我们“分箱”,我们班组,他的未婚妻叫史秀兰,又从我们模具组旁边的过道路过,是有事?还是想多看一眼刘喜芳?还是视察?我们不得而知,只听郭树林小声地开玩笑地问刘喜芳:“喜芳,你看见她,心中是啥感受?”然后,郭树林自己就先笑了起来,刘喜芳“狠狠”地瞪了郭树林一眼。说,“你管呢!”我们知道,此时此刻,刘喜芳这个棒小伙,心里乐开了花。 我们看到:何瑞南从石家庄火车站刚刚调到我们组后,经常有一位年轻女同志,穿得挺漂亮,从我们班组旁边的过道路过,我们知道,她已经来过几次了,人们说,那是何瑞南的未婚妻。是多看几眼?还是有事路过?是视察?大家不得而知。我们知道,此时此刻,何瑞南君心里乐开了花。 我们看到,我们住27号单身宿舍楼时,经常会给搞对象的工友,让出房间来,对方总是不好意思地先说,“我对象一会儿要来,你们是不是?”啊、啊、啊。然后,我们一分一秒地也不磨蹭,赶紧离开房间,到楼下无目的地去遛弯。遛啊遛,遛啊遛,遛了两三个小时。我们知道,此时此刻,我们这位工友,心里乐开了花。 我们看到,不经意间,在星期天的“赶集”的路上,看见小成和小玲成双结对地去“赶集”了,爱情已经昭告天下了,我们还没等弄明白,“昨天,这小子不是还没对象吗?”这么快。小成赶紧说:“你好,你好。今天天气,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弄的我们倒不好意思了。我们知道,这位哥们,此时此刻,心里乐开了花。 我们看到,一单身哥们,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看电影,因为每周有一场电影演出。今天,又演电影了,早早的,这个哥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人们从惊讶中似乎明白了什么?啊,人家陪女朋友去看电影了,“啊、啊、啊,这么快!”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位哥们,此时此刻,心里乐开了花。羡慕的我们,不得了,不得了。 在“分箱”里,涌现出了很多夫妻。例如:我们“分箱”的崔玉成、吴青霞伉俪;团支部的王步雷、吴兰英伉俪;铣工组的杨国斌、王杰伉俪;车工组的曹定国、李亚兰伉俪;我们组的刘喜芳、史秀兰;我们一同进厂的张国华、王保良伉俪等等;本“分箱”里大概有十余对,他们在“”分箱相识、相知、相恋。 他们成家后,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是“同厂做工常相伴,每日双双把家还”。穿一身同样的工作服,宛如是他们的“情侣装”。 兵工厂丈夫,基本上全是五好丈夫,模范丈夫。这个兵工厂,女少男多,比例十分悬殊,造成许许多多男士在工厂找不到对象。有一组数据可以计算:年,21--30号楼是男单身宿舍楼。共有10座男单身宿舍楼。而10号楼和31号楼是女单身宿舍楼,仅仅才有2座单身宿舍楼。男单身宿舍,除去少部分原京字九五二部队的老兵外,他们约占男单身职工的五分之一。有人统计过,该厂男女青年比例,是4:1,比例多悬殊,以至于造成男青年找对象难,不是一般的难。因为工厂附近没有任何单位,除了农村外,基本上是无人烟地带。 从恋爱,到结婚,工厂这些女青年,来到工厂,似乎一下子掉进了蜜罐里头,周围的男士,全都是“甜言蜜语”。结婚后,当然了,男青年要兑现承诺,要主动承担家里全部家务,样样表现都是“五好”。有人说,还有“六好”的。已婚男青年全部会做饭,女同志基本不做饭,男青年不会做饭的,也是现学现做,也是整天研究菜谱,烹饪手艺,已婚男青年,还互相交流着做饭经验。工厂有句非常著名的顺口溜,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这句顺口溜就是“男人在家做饭,女人外边锻炼”。不信,如果你要验证一下,你可随意问一位在工厂已婚男士,问他在家做饭否?他肯定是一边哈哈地笑着,一边回答:“做饭吗,简单,做饭吗,简单。”男士全部会做饭,这是这个兵工厂最大的一个特点之一。 “同出同归”可以这样形容他们的生活方式。每天,迎着晨曦,他们一起去上班,伴着落晖,他们一同归家。工作间隙里,对方一个鼓舞的眼神、一个会心地微笑,就让他们彼此心满意足。 “他们的生活挺平凡的,且蛮幸福的。”许多人这样赞叹道。这些夫妻,生活波澜不惊,朴实无华,他们携手努力工作,日子在平淡中美好幸福。 恩格斯说:“爱情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权利。单相思不是爱情。道理很显然。 我的同“分箱”有一位好朋友,叫辕子,我们一直是挚友,在兵工厂中来往较多,闲暇时,他给我讲了他自己的爱情故事。我稍微整理了一下,从这个故事中,可以从一个侧面,一睹当年的同事,以及你、他、她。 附:辕子的爱情故事 他说: “人生中有许许多多的事,让人一直难以忘怀。记忆起我当年“分箱”的爱情故事,就是如此。今天回想起来,心中依然充满了怀念、幸福和甜蜜。我进兵工厂是二十世纪的年,正好21岁,当时到了远离市区的兵工厂,是一个巨型兵工厂,兵工厂有几千人,大多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充满了朝气和追求,充满了理想和憧憬,充满了幸福和美好。 大家在一起工作、学习、活动,天长日久,相互之间总不免产生情愫。在我眼中,当时兵工厂里的女孩子都很漂亮、散发着青春少女迷人的魅力,让人眼花缭乱,不能自已。 勿庸讳言,我对其中好多位女孩子,就产生过刻骨铭心的爱恋之情。 第一次,单相思,心动。 记得进厂不久,一天,我正在“分箱”干活,一位女同事突然从我面前走过。她年纪与我相仿,身材高挑,皮肤白晳,特别是脸庞两腮淡淡的红晕,特别好看。黑黑的眼睛,如深水潭般地清幽、明净,轻轻一动如波光粼粼,让人心醉。一头秀发随意地披散在后背,显得那么自然、秀气,我当时眼睛一亮,久久地呆立在那里。 过后,向学习的师傅打听,师傅说,她是本“分箱”的“丽”,她的工作干净、清闲,再加上她长得漂亮,所以说,是当时公认的“厂花”,也是“分箱花”之一。从此,我在心目中就开始暗恋她,精心设计和她说话相遇的情景,幻想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微笑。有时,我远远看到她,心中就会情不自禁地想上去和她说话。 一次,大家在一起说笑时,她过来问我的名字,让我心生荡漾,激动好长时间。她在我心中如女神般的圣洁、美丽,我自感卑微,不敢有半点亵渎,只是把这种爱默默地埋在心底,日夜思恋,刻骨铭心。听说她找对象条件很高,我一个普通工人,可望不可及,最终只看到她“花落人家”,嫁了一个军人。我心中惋惜、懊悔、痛苦、失望,长时间的不能平静。 那一阵儿,我一个人经常在兵工厂的北山上苦闷,徘徊,很久、很久。我想,这也是青春一种爱的萌动,也算是我人生的“初恋”,或者是单相思。显然,只是一种单相思而已。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第二次,态度不主动,但又一次心动。 不久,新来的一位女同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虽然长相平常,与当年那位不能相比。但文静好学,举止稳重优雅,也同样有一种风韵。我们很谈得来,理想、人生、学习、工作,虽然没有谈到爱情,但心里也算是有点意思,只不过是保持各自男女之间的一种矜持而已。而我更是怕受到拒绝,心里承受不起爱情的又一次打击。后来,她嫁了一个军人。直到许多年以后,已各自成婚的我们,笑谈年轻在一起的话题,才敢坦陈当时互有爱恋的心情。然而时过境迁,爱情成了我们之间永远的友情。 第三次,互相动心,但对方家长不同意。 年初,我们组里的一位大姐,帮着我介绍了兵工厂里另外“分箱”一位女同事,她人淳朴内向,也长得比较漂亮。开始,大姐安排我们在兵工厂礼堂后边见面,后来,她说不方便,我们又去省城见面,彼此倒也觉得合适。可是没多久,她父母知道了此事,认为找我不合适,因此,不同意我们的往来。虽然自己女儿也是工人,但“人往高处走”,也可理解。女同事一步一回头地不愿意离开我,但她是个乖孩子,最后听父母的话,也嫁了一个转业军人,此次的爱情,只有结束。 然而,我也知道,当时兵工厂里,也有其他女工友,对我有好感,她们帮我做了很多事,与我谈了许多“心里话”,好像有意无意之间,在暗示了什么。最后,也燃不起我的激情,不了了之。 第四次,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在苦闷中,年底,一位女工友吸引了我。平常,她对我就比较好,只是我没看出来,我对她说了几句暗示的话后,看得出来,还差不多。这一下,燃起了我爱情的火苗,我打定主意想追她。正好,一位同“分箱”的一位老大姐,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当了红娘,经这位红娘的介绍,我们双方都没意见,这也算是有缘份吧。在大家的一片祝福声中,我们两个很快坠入爱河,后来,她成为我的妻子。 老人说,这就是我婚姻命。一路走来,我感觉真的好幸福。今天,我已经退休了,回首恋爱往事,我无限感慨,无比怀念过去的人生岁月,特别是“分箱”的那段时光,那段青春的爱情,在我心中永远年轻。当年的“分箱”爱情,我永远地藏在心底,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本段爱情故事请勿对号入座) 08 第二食堂 上图为第二职工食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工厂共有四个单身食堂。每个食堂,大概有三四百人吃饭。这里每天人山人海、人来人往。我上职工大学以前,是在第三职工食堂吃饭,也是“”分箱的定点食堂。上了职工大学后,就改为第二食堂了,因为它是职工大学的定点食堂。 图片上的门口的右边位置,有一个大树,夏天,我们七八个职工大学同学围在大树下,在那里吃。当然是蹲着吃了。 平常吃饭的位置,是一进门右边的三四张桌子。一张桌子坐七八个人。都是长条凳,长条桌。凳子连在桌子上,不吃饭的时候,可以把凳子翻上来,翻到桌子上。如果去得早了,有座位。去得晚了,就没有座位了。去得晚了之后,就端着馒头、玉米面饼子、菜盆,来到门口吃, 看到这张照片,仿佛我们就在食堂里买饭,吃饭。看到这张照片,仿佛我们就在门口的大树下,蹲着吃饭,一边吃,一边讨论着课堂上所讲的问题。看到这张照片,仿佛在食堂的门口,上了二楼的一间房间里,买饭票,一个月只能买33斤的饭票。早饭、午饭、晚饭,都在这个食堂吃。职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兵工厂技术部门,还是定点在这里吃饭。 那个时候,每个人每个月的伙食是国家定量供应的。国家实行的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市场上没有可以随便购买的粮食。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每人每月发粮票,干部、教师、医师每人每月27斤,居民24斤,工人按工种:特殊工种45斤,一般体力劳动工人30到33斤等。肉票每人每月1斤,1斤肉票可以买1斤鸡蛋,油票每人每月4两,这些票都是按人头发放的。 每个人定量供应的粮食,有粗粮,有细粮,粗粮多,细粮少,粗粮占到80%,细粮占到20%,粗粮是高粱米、玉米面,细粮就是白面,还有大米,每人每月一斤肉。我每个月定量为33斤,这就需要精打细算了,否则吃不到月底。每天要计划着吃。严格控制,每天吃一斤粮食。 下面是每天的伙食标配。早晨,是两个窝头,窝头或是玉米面,或是高粱米;这就是4两粮票,一碗粥是一两粮票,粥是玉米面、小米、高粱米等。半斤粮票没了。一份咸菜,咸菜就是腌大白萝卜,腌红萝卜。 中午是两个窝头,还是4两粮票,一份菜。这一份菜,冬天就是素炒大白菜,有时候加点油梭子,有时白菜豆腐,还有白萝卜条,春天是菠菜粉条,炒豆芽等,夏天就是炒西红柿、茄子,土豆、黄瓜、绿辣椒,价格就是一毛钱,二毛钱。 晚上是一两玉米粥,一个窝头,一分钱的咸菜,这就是每天的标准伙食。那个时候我很瘦,体重在60公斤左右。就是在食堂里能吃点肉,也是肉梭子之类的,食堂最贵的菜是三毛钱。肉梭子,油梭子就是先把肥膘耗出油剩下的残渣。几百人在那里吃饭,炊事员用大铁锅炒菜,大铁铲子拌菜。那时,厂部组织后勤的同志们,千方百计找米、面、肉、鱼的货源,满足职工午餐和晚餐,而且,为了职工能吃好,各种炒菜、熟食准备了很多,粗粮花样也有十几种。那时生活困难,职工吃肉包子和饺子就感觉特别好。 火车上的烧饼,也成为我的日常伙食标配。我的未婚妻,从年起,一直到我调离兵工厂的年底,从火车上经常给我买一大袋烧饼。买火车上的烧饼不需要粮票,5分钱一个,这样,可以补贴我的口粮不足的问题,足够我在兵工厂吃一个星期了。宿舍里有袋装的郑州大米,也是她捎来的。她是北京至郑州区间的铁路列车员。年底,逐渐吃饭不要粮票了。我在这里吃了八年的饭,直至调离这个兵工厂。 09 周日回家 这是没有照片的一个章节。也是很难忘的一个片段。在学徒期间两年多的时间里,除去在集训队培训的三个多月没有回家外,其他的时间,周日我们几乎没有在厂里呆过,原因有二。一是当时计划经济,粮食定量供应,我们这些小伙子们,一个月33斤粮食,真的是不够吃。在加上是在食堂吃饭,恐怕就不是33斤的粮食定量了。有人说,一顿大米饭,吃了八两,才刚刚吃了个半饱,一天还有两顿饭,那怎么吃呢?为此,职工们经常上书工厂领导,要求食堂给足分量。工厂领导为此,多次深入到食堂,现场办公。 在食堂吃饭,总是和不满意相提并论。职工的吃饱与否,也总是与上书领导相伴。有一年,在年底评比先进时,第三职工食堂被评为先进食堂,这时候,在第三食堂门口,发现一张小字报,上面写到:“三食堂真正好,八两大米吃不饱。不是我们吃得多,而是他们给得少。”后来,这件事,引起工厂领导重视,工厂政委宋树诚在大会上对第三食堂提出严肃批评,,此后一段时间,食堂的分量给足给够了。 工厂有定量,吃不饱。反之,回家是可以吃饱饭的。第二个原因,星期天,在厂里,无所事事,还是回到省城和家里人在一起,有意思。所以说,几乎在这两年多的期间里,在工厂过星期天,很少。那个时候,是休息一天。 说是回家,其实回家的路,是非常麻烦的。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工厂远离公路,远离铁路,离公路有十来里路,离小火车站十来里路。周日回家,乘车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坐汽车班车,一种是下班后坐火车。 坐汽车班车,星期六工厂下午下班后没有班车,只有下午13点钟的一趟班车,坐这个班车的人很多,平常,票比较好买。可到了星期六,大家都急着往外出门,所以说,票也非常难买,卖票的是在运输队旁边的一个小站房里,规定上午11点在那里售票,买票的人非常多,窗口开了没多长时间,卖了也没有几张票,就没有票了。车队看乘车的人非常多,有时候,就临时再增加一辆班车,以解大家燃眉之急。班车票价是五毛钱。所以说,乘汽车班车就不是大多数青年职工的选择。原因一是要请假半天,二是票也不好买。 所以说,大多数青年职工只能乘火车回家,当时有一列火车快车从工厂附近这个火车小站经过,是每天下午的18:40分到站,我们必须提前半个小时下班,换上衣服,17:30到工厂运输队集合。到了这个时间,乘车集合的人很多,总有二三百人,坐上工厂准备的嘎斯,车牌号“甲**”军用大卡车,就直奔火车站了,青年工人特别多,大家几乎都是如此回家。所以工厂准备的军用卡车也就特别多,有三四辆。去火车站的时候,有时还乘工厂的铁路小电车去,工厂有一条铁路线,坐上小电车,直通小火车站,小电车很方便。电车大小就像一辆公交车一样,可座位不多。 到了小火车站以后,就赶紧买票,火车票价格是六毛钱,买了票以后火车也就到站了。大家坐上火车,在车上开始打扑克。19:45就到了省城火车站,下车后,大家就各奔自己的家了,到家时间一般都是晚上21点钟左右。春夏秋冬都是如此。夏天好像人们还没有睡觉,还在外面乘凉,大街上人也很多,到了冬天,晚上21点多钟,大街上行人车辆很少了。那个时候,星期天只休息一天,没有休息两天之说,就是星期日休息,星期六不休息。 从工厂回家是这样。但要想从家里回到工厂就更麻烦了。就拿乘火车来说吧,基本上,每次从家回工厂要过两道关。第一道关,就是想办法要买到火车票,买不到火车票,就要想办法要进入到火车站站台内。这是第一道关。第二道关,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挤上人多的火车。第二天晚上,也就是星期天的晚上20:30,我们到省城火车站售票处集合,这是大家约定的时间,有时候,能买上火车票,有时候是买不上火车票的。买不上火车票的时候,大家就各想各的办法,分别从不同的车站入口处,进入到车站站台内。有的是从铁路职工通勤口,进入站台,有的是买个站台票进入站台,还有的是找熟人进入站台,来不及的,干脆就翻墙头了。等等,大家没有办法,因为第二天都要赶着上班。 这趟火车,自始至终,趟趟人满为患,进入到站台上,还要挤上火车,大家使劲挤啊挤。后面的人拼命往前挤,前面的人都上不了车。下面的人拼命推。在车上,再一轮感到了拥挤。车里堆放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还会有人抽烟,争吵声、说话声、吵闹声时不时传来。这真是名副其实的人挤人、人堆人。过道、洗脸池、门边到处挤满了人,人挨着人、挤着人,连挪脚的地方都没有。“挤火车”,很辛苦。 我们坐的这趟火车,是每晚21:20从省城开车,到我们的小站时间是22:40左右。下了火车,乘上工厂为我们准备的嘎斯,车牌号“甲**”军用卡车,嘎斯卡车是专门来接我们的,每次有三四辆之多。大家坐上卡车就回到厂里了。有时,接我们的是铁路小电车,拉着回到厂里的时间是晚上23:30左右,大家洗一洗,就半夜了,赶紧睡觉。第二天就又投入到了新的战斗工作中去。 这就是周日回家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几乎每周都在上演。后来有的人谈恋爱了,有的人结婚了,回家的年青人相对就少了。到年左右,乘火车回家的人,还有一百多人左右。这里,凸显了三线兵工厂交通的不便。 我的三位工友:刚子、小民和小杜。一次,刚子和小民、小杜聊天,说起在火车站翻墙头回厂上班的经历,他们说,那是印象深刻,刻骨铭心。也是令人难忘的。小民说:“正是在翻墙头时认识了刚子,年轻人,痛苦并快乐着”。 刚子说:“我那时,有时也骑自行车回家,回来时,困难不可想象。骑车从省城钢厂往返工厂,在星光中,常常被蝙蝠追逐,进入山区后,“夜神”仍不愿意离去。当我在用之字形的方式,翻越一段十多里的上坡路时,多么希望过来一辆拖拉机啊。一次碰上了一辆55式的拖拉机,不用商量,就粘上了,那伙计可能嫌我没言语,开得飞快,我岂肯放弃。” 刚子说:“还有一次,骑行从家返回到工厂附近河边时,要迟到了,因家里琐事,精力不集中,手扶在车把上,一个鹅卵石把我撂倒了,裤子摔破了。远处一位老农纳闷,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这人咋了,然而,我爬起来还得直奔办公室。”刚子接着说:“坐火车回厂,经常是在众民工的紧密拥抱和裹夹中酣然入睡。到站后再奋勇下车,跟着人群直奔电车或嘎斯军车。” 小民接着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常常出现这样一场情景剧。星期六下班后回家,在离工厂十来里的国道公路一个路口,男的猫在路沟里,美女们出面截车,卡车一停或稍慢,众好汉夹着行李,在夜幕的掩护下,如飞虎队员一般,飞奔上车,到省城市郊再择机下车。有一次车上装的是粉煤,那就惨了。说到此,可能大部分人没此磨难,但那时这些年青人是“痛并快乐着”。”这不是实景演出,是那难忘的过去。 小杜接着说:“回趟家的确不容易。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新工人,在小火车站,给送我们上站的工厂嘎斯车司机师傅敬烟。”他很客气地说:“侯师傅,侯师傅,抽颗烟”。却见司机师傅满脸不悦。后来,才知道师傅原本姓章,绰号叫猴子。和他熟络的老师傅,就直接称呼老猴或猴子。这位新工人,就把他当成了侯师傅。那时候,工厂里最牛掰的就是司机师傅了。 小民又说:“有时候,家里有急事需要办理,就直接去了运输队,去找一辆车搭车回家。但到了车队,看到一司机,正在发动车辆,准备开往省城,就赶紧上前和师傅搭话,个别师傅满脸不悦。但也并不说些什么,我就只管上车了,搭上他的车就回家了。” 10 和师傅在一起 时光飞逝,一转眼已是四十多年过去了。四十年风雨沧桑路,四十载征程铸辉煌。饮水思源,原京字九五二部队的干部战士辛勤建厂,才有了今日的发展。当年的师傅工友,现在都已年迈,大部分已退休,甚至相继离去的也已不少。 现在,建设美好工厂的接力棒,正一棒一棒往下传。弹指之间,今非昔比,年轻一代,勇往直前,继往开来,兵工厂气象万千,日新月异,工人们正如火如荼的建设、生产,到处莺歌燕舞。 兵工厂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昨天是艰难的,今天是成功的,明天前景更加美好,将更加壮大,将铸就新的辉煌。 “迟拍”的照片,尽管迟了40年,但总算是有了。弥补了心中的空白和遗憾。我们昨天在“分箱”,今天虽然离开“分箱”,但“分箱”永远在我们心中。 我们昨天相遇,今天,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了,但你、我、他、她,却又始终在一起。正像厂长李献洲,在路上,一边走,一边跟我所说的那样:“这是我们人生的一段重要路程,亦是人生旅途中,一道非常重要的风景……” 看久了照片,好像又多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我还在“分箱”里工作,在大摇臂钻床前工作,在“锻模”上抛光,在干活,在工作。不觉得累,不觉得苦,高高兴兴,快快乐乐。 身旁还有许多师傅工友在走过;他们在车床、铣床、磨床前忙碌着,认真切磋着…… 迟拍的照片是有数的,脑海中的照片是无数的,照片内容是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 (名单由张国华、王建民、张发祥帮助提供) 草于年10月 欢迎投稿 联系电话- 邮箱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eiguihuaa.com/mghpl/6068.html
- 上一篇文章: 玫瑰醋的功效与作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