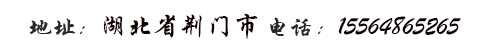无论乱世流年还是柴米油盐,有一束花,生活
|
一个再平凡的家庭,只要有了花,就会有勃勃生气,就会有生活的体面。让花说出我们的爱吧。 无论乱世流年还是柴米油盐 有一束花,生活就有了体面 文 群学君 01 在昆明盘桓几日,印象最深的,不是荷塘云影翠湖春晓,不是赫赫讲武堂,也不是金马碧鸡流光溢彩,而是昆明城北郊一个破破烂烂的城中村。 蜿蜒扭曲的巷道,各式怪异丑陋的楼房,如蛛网般架设的天线,兼做公共澡堂的小旅馆,尘土飞扬的停车场,网吧、小吃摊、菜市场和路边闲坐负喧的老人,这是一幅被快速现代化与城市化遗落的标准画面。 △ 昆明北郊棕皮营城中村一隅 村口醒目的“拆迁改造”标牌,正在昭告所有此地居民:没多久,我们也会脱胎换骨,旧貌新颜——五百米开外鳞次栉比的高楼,房价已经快要接近两万。 △ 棕皮营城中村入口 这个地方现在的地名,叫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延长线棕皮营,整整八十年前,这里叫做昆明市龙泉镇棕皮营桂家花园——我一大早从呈贡一路开了40公里,就是为了来找这个花园。 辗转走到这个破败区域的腹地,终于看到那个荒草萋萋的小院和院中两间低矮小屋。尽管周围的桂树早就灰飞烟灭了,桂家花园也不复当年光景,但只要有这两间小屋在,那个年代遥远的花园,和它代表的一个时代的斯文和体面,就从来不曾远离。 △ 桂家花园旧宅,几经辗转保留至今 八十年前,这座院落的主人,先生叫梁思成,太太叫林徽因。 这一对中国建筑史上最著名的夫妻,这一对发现了佛光寺,重写了建筑史,设计了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夫妻,一辈子却只有一次机会,给自己设计一座住宅,如今这座房子就在我眼前:简陋,局促、窘迫。 有建筑学家来看过这房子,说了一句话:对于既对建立中国建筑的古典主义传统有着终身追求,又对中国古代建筑毫不顾及永久性持批判态度的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来说,这座他唯一为自己设计的小瓦房,具有一种“强烈的讽刺性和悲剧性”。 △ 梁思成林徽因旧宅已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大概不会像他们在北京的故居那样,遭遇强拆的命运。 我没那样严谨到苛刻的理性,也没有丰盈得葳蕤的浪漫,有的只是一种突然涌上心头的感动。年中秋,林徽因给她最要好的外国朋友,费正清教授的太太费慰梅(“费正清”这个中文名字,是梁思成取的,而“费慰梅”,则来自林徽因的建议)写信: 出人意料地,这所房子花了比原先告诉我们的高三倍的价钱,所以把我们原来就不多的积蓄都耗尽了,……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一根钉子而奋斗,为了能够迁入这个甚至不足以“蔽风雨”的屋顶之下,我们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 时光是琥珀,悲欢被封锁。尽管周围为生计打拼的外乡人,不再懂得这座八十岁老屋的沉吟低语,但当我站在它面前时,依旧能触摸到烽火连三月的惊心动魄,和国难当头时两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性、坚韧和从容不迫。 △ 梁思成林徽因旧居一隅 02 建造这间瓦舍,林徽因对梁思成提了两个要求: 第一,要有一个壁炉。昆明地处高原,冬天阴冷,夫妻俩身体不好,还有老幼随身,有一个壁炉,会温暖许多。更重要的,有了壁炉,一同南下的当年“太太的客厅”里那些朋友,就依然不会星散。 金岳霖——梁思成夫妇都亲昵地叫他“老金”,就住在隔壁一间耳房。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周培源、朱自清、冯友兰、陈岱孙……先生们又聚到这间小小的客厅里,战火硝烟中,这间瓦房有一个如天地般宽广的精神世界。 △ 旧居中依照原样复原的壁炉 △ 朋友们在昆明。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两个小朋友,是再冰、从诫。 第二,要有花。林徽因终身爱花,她一辈子写了几十首诗,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花”。昆明又是个四季如春的地方,南渡的北方人,几曾见过这么多鲜艳明媚? △ 旧居砖墙外,依然有鲜花怒放 整个抗战期间,林徽因只发表了一首诗,就叫《除夕看花》。 那是年除夕,桂家花园的这座新居落成,林徽因从花市买来雪白的碧桃和殷红的山茶。有了花,再艰难的岁月,也有了生的喜悦,有了过年的味道: 新从嘈杂着异乡口调的花市上买来 碧桃雪白的长枝,同血红般山茶花。 着自己小角隅再用精致鲜妍来结彩, 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剩余下! …… 如果心头再旋转着熟识旧时的芳菲, 模糊如条小径越过无数道篱笆, 纷纭的花叶枝条,草香弄得人昏迷, 今日的脚步,再不甘重踏上前时的泥沙。 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零乱, 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刻画, 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 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 △ 林徽因与女儿再冰,在桂家花园旧居前。 我在想,时事那么艰难,林徽因为什么还那么执着于客厅里那一束鲜花?仅仅是文艺青年的情怀,抑或富家女的傲娇? 也许多少有一些,但更重要的,正因为有这一束鲜花在,我们就依然能感受到离乱流年里那一代人不屈和乐观,斯文和体面。正因为有这一束鲜花在,生活就依然是色彩明媚的。 走出城中村,河堤上成排的林木,倒依然如林徽因描述的那般,用它们的枝条,擦拭着昆明的天空,一碧如洗的天空。 △ 年,林徽因回到昆明。她被病痛折磨得憔悴、苍白,不再年轻,却依然很体面。 03 回到南京,从清爽一头栽进溽热,日子又从浮想联翩堕入柴米油盐。无论林徽因的客厅里的山茶,还是沈从文笔下翠翠梦中的虎耳草,终究还是要变成每天篮子里的青菜萝卜茭白毛豆,《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朱砂痣、白月光,也终究沦为墙上的蚊子血、襟口的白米粒。 总归是有点失落的,但幸好,还有花。 我的一个朋友,十年前一场车祸,九死一生。手术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在护工的搀扶下,在医院神经外科的走廊上慢慢走走。夜深人不静,病区里四下都是垂死呻吟的声音。从走廊尽头的玻璃窗看出去,路边伞状的路灯下,一树玉兰花像一群扑着翅膀的鸽子,仿佛挣扎着要活下去。 朋友说,从此,他就喜欢上了花,无论什么样的花,都让我觉得精神,活力,优雅,多看一眼仿佛能吸收能量似的。哪怕是细小的阿拉伯婆婆纳,都让我觉得精致有精巧,淡蓝色一片铺满山野。更别提街头橱窗里那些大把大把的玫瑰和月季,简直像是按了静音的舞蹈和狂欢,来,爱我,爱我。 那以后,他结了婚,太太是设计师,也画油画。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在南京大学受训,晚上走出校门,都会在一家小花店买一束雏菊和桔梗,在地铁站台上等着的时候,怀里的花束散发着朦胧的光。回到家插在餐厅或者卧室,当作给太太的礼物。而太太的回赠,就是一幅幅静物,主题都是花:温暖,明媚。 朋友的妈妈,和大部分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样,一生节俭,常常抱怨他把钱浪费在买花这种“没用”的事情上。 有一天,他妈妈在收拾餐桌——桌上是他新买的一捧马蹄莲——她踮起脚,偷偷地闻了闻白色的花苞,露出小学女生厌恶同桌似的神情,自言自语地说:这花不香啊,不过还是挺好看的。 接下来的几天,下班回到家,马蹄莲都已经换过了水,并且剪掉了开裂的底部。一个不喜欢花的更年期妇女,最终还是勤快地打理起餐桌上的插花。 一个再平凡的家庭,只要有了花,就会有勃勃生气,就会有生活的体面。 04 当柴米油盐的生活常态,渐渐取代怦然心动的刹那惊艳,也许我们也会对鲜花有不同的定义,但总不会被取代。就像夏洛说:向日葵这寓意好,它象征着永远朝着太阳,阳光,浪漫!马冬梅说:不是,主要能吃。 每个人对于鲜花的需求,用鲜花去表达的心意,都有自己的态度和解读。但是在某个场景,某个时刻,某个状态下收到的鲜花,是可以点亮那个瞬间记忆的小火苗,并将长久保存在记忆里,蔓延到未来的人生韵味里。 我的那个朋友,也是个爱折腾事儿的汉子,他自己做了个书店,名字很奇怪,叫“象甲”,我至今没弄明白这名字是什么意思。不过,他的真性情,让我很感动。 不久前,“象甲书店”和南京最大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eiguihuaa.com/mghfz/8850.html
- 上一篇文章: 教育,不是成为强者,而是懂得宽恕
- 下一篇文章: 美哭了潜江middot碧桂园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