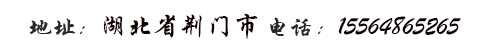战后建筑类型学的演变及其模糊普遍性
|
撰文:QuicksandJiang+DaseinChen 摘要二战后由阿尔干、穆拉托里、艾莫尼诺、格里高蒂、罗西等人推动的类型学研究植根于卡特梅尔?德昆西对“模型”与“类型”的区分。简而言之,“类型”与“模型”的区别在于,模型是精确的,并能直接转变为另一个物体,而类型仅具有一种模糊的普遍性。罗西将这种带有模糊性的类型学看作通往城市建筑的本质。文章对“模型”与“类型”的词源进行了回溯分析,尝试探清其在建筑理论和设计中的源流演变,通过展现这些意大利学者对城市建筑的历史研究,反思“模型-类型”对当代建筑学研究的价值。关键词模型;类型;普遍性;设计原型;类型学AbstractTheemergingtypologypromotedbyG.C.Argan,S.Muratori,C.Aymonino,V.Gregotti,A.RossiafterWorldWarIIhaditsrootsinthedistinctionbetween“model”and“type”byQuatremèredeQuincy.Brieflyspeaking,what“type”distinguishesitselffrom“model”isthatmodelcouldbeprecise,specificanddirectlyturnedintoanobject,howevertypeonlypossessesakindofvaguegenerality.AtypologywithinwhichsuchvaguenessisfoundwasregardedbyRossiastowardstheessenceofurbanarchitecture.Thisarticle,basedonaretrospectiveetymologicalanalysis,triestoreviewthecontinuousandevolutionaryreflectionson“model”and“type”inarchitecturaltheoryanddesign,fromwhichwecouldbenefitincontemporaryarchitectureresearch.KeywordsModel;Type;Generality;DesignPrototype;Typology某一类理论的兴起必然基于某个时代背景,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并且通常都会形成相应的学术群体。在建筑学理论中,类型学在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崛起与两类问题有关。第一类问题关于设计的方法论(DesignMethodology),其中典型代表是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Alexander)的模式语言(patternlanguage)。这一理论将设计视为形式(form)与环境(context)之间的纽带,研究设计方法论的目的是寻找生成设计的机制。模式语言下的设计行为对功能需求进行综合,并用形式来满足这种需求[1],它指向一种划分层级与穷举个例的类型学。阿兰?柯洪(AlanColquhoun)在《类型学与设计方法》(TypologyandDesignMethod)中指出,在缺乏有效的分析与分类工具的情况下,当建筑师处理不了复杂的问题时,他们倾向于借助之前的范例来解决新问题。这提供了一种类型学的解决思路,将其视为一种直面设计问题的手段[2]。第二类问题关于城市重建或新建中的历史向度,与场所和集体记忆有关。20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北部,以卡洛?阿尔干(GiulioCarloArgan)、穆拉托里(SaverioMuratori)、艾莫尼诺(CarloAymonino)、格里高蒂(VittorioGregotti)、阿尔多?罗西(AldoRossi)等为首的学者圈(图1)将类型学发展为一类进行城市建筑调研与设计的方法,并以此表达对城市历史研究的立场。他们对类型的理解各有差别,但共同点是,“类型”概念或多或少带有理想化的特征。这一种类型学思考指向建筑的本质问题,本文将就此展开回溯研究。 图1_讨论建筑类型学与城市形态学的意大利圈子主要成员 (一)模型与类型:从德昆西到阿尔干19世纪上半叶,卡特梅尔?德昆西(QuatremèredeQuincy)沿袭法国学者喜好编纂百科全书的传统,出版了两部辞典:《方法论辞典》(Encyclopédieméthodique)(—年)与《建筑学历史辞典》(Dcitonnairehistoriqued’architecture)(年)。这两部辞典均收录了一个词条——“类型”(type)。德昆西理论建树的基础是他一贯擅长的词源考证与概念辨析,关于“类型”这一词条,他首先写道,“类型”(type)这个词源自古希腊词语“typos”。根据普遍的用法,这个词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所具有的一些差异。“它基本覆盖了“模型”(modèle)、“模具”(matrice)、“印章”(empreinte)、“范”(moule)、“浅浮雕”(figureenreliefouenbas-relief)等词里面的大部分含义。[3]从古希腊词源来看,“模型”(model)与“类型”(type)之间的关系比较笼统,相互涵盖。即使在德昆西所处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语情境中,“type”这个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普遍地被当作“类型”来使用,相比之下,更常见的词是“genre”(种类)[4]。换言之,当时的建筑著作每当要进行分类或者概述类型的特征时,更习惯使用“genre”。当一门语言处于转型期,新的定义通常会包裹之前的语言习惯出现,并且被注入更新后的理解。德昆西紧接着描述了“模型”与“类型”的区别:比起“模型”(modèle),“类型”(type)这个词没有那么多地呈现出可供拷贝或彻底模仿的物像(l’imaged’unechose),而更多的是有关各个要素的思想,这种思想本身就应该作为模型里的法则。因此我们不会说(至少这种说法可能是错的),一件雕塑或是一幅绘画的构图是其临摹对象的“类型”;但一段残片、一张草图、一位大师的想法、一段多少显得模糊的描述,在艺术家的想象中催生了艺术品,我们会说“类型”由这样的想法、母题或意图酝酿出来。“模型”则被理解为与艺术作品的实际操作相关,它是一类可被重复的物体。相反,“类型”与不同人对艺术品的创作方式有关,这些艺术品无相似之处。“模型”中的一切都是精准的、确定的,而“类型”中的一切却多少有点模糊。[5]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这段话的涵义,首先要厘清“模型”与“类型”的中文定义。在此以“形”、“型”二字的辨析作为出发点,考察它们在中文语境里的差异[6]。从字源上看,我们可以将作为名词的“形”理解为一种具象的、可被直接描摹的对象,而描摹过程是一种象形化的仿造。“型”字意符从土,本义为“鑄器之法”,即用泥土制成的铸造器物的模子,后亦引申为类型、式样、楷模等。从字源上看,“型”并非一个具体可描摹的对象,这一点跟“形”不同;“型”是一种带有控制性的原则系统,一种产生形式的发生器(generator),而不是可呈现的形式本身。因此,获得一个具体的“模型”并对其进行模仿、复制,可谓之“象形”;而将一套生成形式的法则、一种抽象而模糊的“类型”作为设计的发生器,则谓之“炼型”。德昆西的《建筑学历史辞典》的意大利文译本出版于年,之后,“类型”这个概念一直都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讨论。直到年,意大利艺术史学家卡洛?阿尔干才根据德昆西的词条做出了新的解释。阿尔干在《论建筑类型学》(Sulconcettoditipologiaarchitettonica)中,将建筑学中的类型学与具象艺术(figurativeart)中的圣像学(Iconography)做了类比[7]。他认为从操作层面上看,建筑设计与艺术创作是平行的。在这一点上,阿尔干延续了德昆西对“类型”的理解,即认为类型首先存在于某种模糊的艺术创作过程中。在德昆西的理论基础上,阿尔干进一步提出,“类型”应当被理解为形式的内在结构,或者是某种原则,它包含了无限种可能的形式变体(formalvariation)以及对“类型”自身更进一步的结构调整。与德昆西不同的是,阿尔干提到了“类型”的形式变体,他认为“类型”是后验的(aposteriori)[8]:“类型”的这种模糊性(vaghezza/vagueness)或普遍性(genericità/generality),使之不能直接作用于建筑设计或形式操作,这也解释了一种“类型”是如何形成的。“类型”从来不会先验地出现,而总是从一系列的案例中演绎而来。所以一座圆形神殿的“类型”从来不会跟具体的这座或者那座神殿相同,而是所有圆形神殿的差异与融合的结果。因此“类型”的诞生依赖于一系列建筑的存在,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形式与功能上的可类比性。据此,拉斐尔?莫内欧(RafaelMoneo)明确指出阿尔干排斥了德昆西的“类型”概念中的新柏拉图主义成分。这是阿尔干在德昆西的“类型”概念的基础上所做的最突出的改进和贡献。德昆西谈的是理念化的基本原则,阿尔干则开始偏向于类型学在历史与设计中的应用,而非仅限于理论方面[9]。德昆西认为“类型”虽然存在但模糊不清,它不是一种确定的形式,而是一种图式(schema)或是形式概要(outlineofform)。阿尔干认同这一点,但进而补充,“类型”总是从历史经验演绎而来的。通过“演绎”(deduction)而不是“归纳”(induction),阿尔干尝试探寻“类型”的模糊性与普遍性如何存在于众多历史个案中。对他来说,“类型”不仅仅是理念上的原则,还必须带有实体化的一面。阿尔干对“类型”的重新定义削弱了这一概念在德昆西理论中的形而上学色彩,此后的学者也将这一点成功转化为建筑设计中的方法,并应用到城市的历史研究中来。阿尔干在文章最后提到,将“类型”预设为建筑师工作的起点,并不断绝建筑师与历史的关系。这也不阻止建筑师选择或是拒绝将某一些具体的建筑作为模型。阿尔干据此将设计、历史、理论这三个维度在类型学中联系起来,提升了这一概念的方法论价值。(二)六十年代的“建筑类型”研究:穆拉托里、艾莫尼诺与罗西阿尔干从艺术史和建筑史的角度改进和补充了“类型-模型”的定义,并指出建筑类型学在理想主义层面仍然具有意义。在此基础上,艾莫尼诺、罗西等人继续发展建筑类型学。二战后,以穆拉托里为首的学者在展开历史城区调研的过程中,开始建立所谓的城市形态学理论。城市形态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包括广泛的社会调研,穆拉托里曾重点调研过威尼斯(图2)[10],而艾莫尼诺调研了帕多瓦(图3,图4)[11],罗西调研了米兰[12]。穆拉托里将“类型”看作一种形式结构,它反映不同规模的城市里存在内在的连续性[13]。尽管穆拉托里认同“类型”具有理想化的一面,但他并没有将“类型”看作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倾向于将它看作一种要素,辅助当代人类更好地理解城市是如何生长和扩张的。这种城市形态学的方法通过分析个别要素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来认识城市中的建筑,“类型”主要被用作分析工具。穆拉托里的“类型”理论与阿尔干对“类型”的重新定义并无过多联系。不过,穆拉托里的城市调研方法却在艾莫尼诺与罗西那里得到了延续。 图2_穆拉托里的威尼斯城市调研 图3_艾莫尼诺的帕多瓦城市调研,街区平面 图4_艾莫尼诺的帕多瓦城市调研,联排住宅平面 —年,罗西接受艾莫尼诺的邀请,作为助理教授参与其在威尼斯建筑大学的“建筑的组织特征”(Caratteridistributividegliedifici)课程,并将讲义结集出版:《建筑类型学的视角与议题》(Aspettieproblemidellatipologiaedilizia)(年)、《建筑类型学观念的形成》(Laformazionedelconcettoditipologiaedilizia)(年)和《论城市形态学与建筑类型学的关系》(Rapportitralamorfologiaurbanaelatipologiaedilizia)(年)(图5)。艾莫尼诺与罗西通过这些文本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建筑类型”(tipoedifiliza)的概念。 图5_艾莫尼诺与罗西在威尼斯建筑大学的教学讲义 在《一种建筑类型学的现代观念的形成》(Laformazionediunmodernoconcettoditipologiaedilizia)中,艾莫尼诺的分析清晰地指向诞生了现代布尔乔亚社会的城市环境,涉及新兴的中产阶级以及启蒙建筑师的乌托邦设计。他将“类型”的概念看作在城市环境及使用功能之外寻找建筑最根本特征的途径。艾莫尼诺将这些根本特征分为三类:(1)特定的主题,尽管它的“类型”可能需要适配一种或多种活动;(2)不受外部影响,它的发展变化只与自身平面有关;(3)独立于建筑法规,只以自身的建筑形式作为特征。“类型”被艾莫尼诺当作从上古城市、启蒙时代城市、工业城市一直到当下城市的转变过程中所创造出的新的理想城市要素,比如重要的公共建筑。艾莫尼诺说过:“建筑类型学不存在唯一的定义;它是一门工具,不是分类。”[14]艾莫尼诺与罗西都拒绝将类型学看作简单的分类问题。比如,在他俩大量引用的18世纪意大利建筑师米利吉亚(FrancescoMilizia)的分类法里,建筑的分类标准不以简单地区分使用功能的差异作为基础。艾莫尼诺与罗西的类型学并不完全排斥分类,而是不希望类型学的内在维度被简单的或者是单一的分类标准所掩盖。在《城市建筑学》(l’Architetturadellacittà)(年)的“类型学问题”一节里,罗西认为一切对城市建筑的历史研究都无法绕开类型学。一种特定的“类型”和形式与生活方式有关,尽管它的具体形态在不同的社会里各不相同[15]。罗西将“类型”这个概念看成是永久与复合的,是一种先于形式的逻辑原则。“类型”伴随着城市建筑的形式自主性,反映了建筑作为一种存在的很多状态,[16]。罗西认为它最接近于建筑的本质: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不管是作为在某个历史时段中被遴选出来的结果,还是那些归入形式的各种意图,类型学的形式是为了呈现出那个精确表征形式自身的过程所具有的综合特征。建筑的创新总会显露出某些特定的倾向,然而这并不包含类型学上的创造。倘若我们意识到,类型只能通过一个漫长的时段来塑造,并且跟城市与社会有高度复杂的联系,那我们就能理解类型学上的创新是不可能的。[17]相对于阿尔干及艾莫尼诺的“类型”概念,罗西强化了“类型”自身凝聚的城市集体记忆,明确指出类型学上的创新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历史足够长的“类型”才是罗西认同的“类型”。罗西的“类型”概念以类似于历史范例的方式出现,它的模糊普遍性(vaguegenerality)在于这个具体的历史范例如何能够适配到具体的城市情境中。这种模糊普遍性既指历史范型的普遍适用原则,也指历史范型在使用过程中不需被精确地重复,于是模糊普遍性可被概括为“类型”的典型特征。此外,罗西的“类型”概念还将自主性引入建筑学,这超越了“幼稚的功能主义”(naivefunctionalism)。他的类型学表现出一种带有历史关怀的研究与设计立场,反对那种在意识形态下漠视城市既存环境的态度。后文将进一步阐释罗西如何将他理解的“类型”带入历史研究与设计。(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类型”、理想形式与历史视角简要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学者对建筑“类型”概念的研究后,下文将对德昆西式的“类型”以及它所蕴含的模糊普遍性再做展开。根据从德昆西、阿尔干到艾莫尼诺、罗西的观点,笔者认为,“类型”有四类存在状态:(1)理念,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一种集体理性,从个人的角度看它又可以是艺术家、建筑师的创作;(2)文字,通过概念指涉来描述内在的控制原则,尽管这种指涉存在局限性;(3)图纸、模型或一切表征建筑的媒介,这意味着将理念实体化;(4)实体建筑物或城市建成环境,被漫长的历史筛选、浓缩与凝固。对于在城市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公共建筑,我们需要以“类型”的方式将其呈现为理想的形式,否则应当摈弃;大量重复出现的城市建筑,比如住宅,则无需以公共建筑般的“类型”来规范。形式作为独立于功能、社会关系的要素,理所当然成为表征“类型”理想化特征的一种途径。我们可以按照这类思路列举一些历史上的经典“类型”:希腊帕提农神庙和罗马万神庙、伯鲁乃列斯基的穹顶、罗马的斗兽场;圆厅别墅;19世纪末开始出现在城市郊区的独立住宅。区分“类型”的共时性与历时性状态,有利于辨明“类型”的变体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我们通过具体案例来考察一些经典的“类型”与理想形式、历史语境的关系。哥特大教堂的例子可以佐证“类型”如何出现在共时性的变体中。维欧莱-勒-迪克提出的“理想大教堂”(lacathédraleidéale)其实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系列在同一时期、相邻区域建造出来的哥特大教堂的集合(图6)。巴黎、亚眠(Amiens)、兰斯(Reims)、博韦(Beauvais)、苏瓦松(Soissons)和努瓦永(Noyon)这些城市在兴建主教座堂的时候都有类似的社会背景、建造团队以及委托方式(市民城市兴起、主教财富和权力增加[18]、建筑师与工匠在相邻城市之间穿梭谋生、经院哲学之风盛行[19]等)。这些共同点足以支撑每一个大教堂变体呈现出理想“类型”的吉光片羽。可以说,维欧莱-勒-杜克的理想大教堂是一种被归纳出来的“类型”化实体。一些普遍性的特征转化为具体的形式语汇嵌入每一个个案,比如西立面的钟塔、中殿的尖拱、玫瑰花窗的纹样等。这种模糊的差别好比同一批次烧制的瓷器,入炉之前,瓷匠的手受到脑海里的总体图式的控制,而制坯、刻花、上釉时特意创作出不同的形态、图样和颜色;瓷器烧制完成后摆在一起,差异与共性一览无遗。这些哥特大教堂的剖面轴测并排放在一起,呈现出“类型”的模糊普遍性的共时状态。 图6_哥特大教堂的理想类型 “类型”的历时性维度比共时性遭遇更多历史突变,正是这些历史突变检验了“类型”的理想形式。先例(precedence)对于历时性的“类型”演变来说很重要,它对于后世变体的意义就像一副柔性的石膏反模,每浇筑完一尊雕塑,都可以调整形态再去浇筑下一尊。这副反模的内轮廓好比是形式,只有当这些形式上升为“类型”,被它投射出的实体才具有无限的价值。伯拉孟特(Bramante)设计的坦比哀多(Tempietto)“类型”以及它的先例与后世演绎(图7)是一个形象的案例。坦比哀多具有的若干形式特征,如环列柱廊、鼓座高窗、半球穹顶等,显然依赖一个“类型”,那就是维特鲁威在《十书》的第四书第八章里描述的环柱廊圆形神殿。这座神殿通过某个具体的历史“模型”(比如位于提沃利的斯利比亚神殿)将进行“类型化”的抽象整合,从而使自身同时呈现为“模型”与“类型”。后世的这些坦比哀多变体,体现出一种模糊普遍性在历时维度上对先例的调整,适配具体的历史语境。 图7_“坦比哀多”的原型以及类型演绎 以上两个案例均为公共建筑,我们再来简单地看一个现代住宅设计。翁格斯(O.M.Ungers)在德国马堡(Marburg)设计的住宅项目是一个“类型”的多种变体。马堡像很多德国中世纪城市一样保留了大量平面与立面形态各异的住宅。翁格斯参考了这些住宅的“类型”,并在他的设计中划定网格,在网格里推敲这个“类型”的各种当代变体(图8),表现出各有差异的形式语言。 图8_翁格斯在马堡设计的独立住宅 (四)模糊普遍性与“类比”方法重新回到意大利学者对类型学的研究上。罗西在发展了成熟的“建筑类型”概念之后,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使用类比的方法(analogy)来研究建筑在城市环境中的模糊普遍性,并且尝试将历史转化为设计。他借鉴了荣格(CarlJung)的“类比”思想。荣格在写给弗洛伊德的信里说,“类比”的思维是存在于想象之中,并不真实,虽然静默不语,却可被感知;它不是一种话语,而是一种对过往主题的沉思,一种内在的独白。逻辑思维是在语词中进行思考,而“类比”的思维是有关历史的、未被表达的,并且事实上也无法在语言中得到表达。[20]之后,罗西发展出“类比建筑”与“类比城市”的概念。在《城市建筑学》中,罗西曾引用18世纪意大利画家卡纳雷多(GiovanniAntonioCanaletto)的画(图9),画中的逼真场景拼接了帕拉弟奥的威尼斯里阿尔托桥方案(PontediRialto)、设计于维琴察的巴西利卡(BasilicadiVicenza)以及基耶里卡蒂宫(PalazzoChiericati)[21]。这是一幅想象出来的威尼斯城市景观,三座建筑全是帕拉弟奥的理想类型[22],它们都不在威尼斯,却被共时地拼贴到一个地方,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语境。 图9_卡纳雷多的油画“卡布里奇奥” 罗西从卡纳雷多的画里借鉴了“类比城市”的手段——寻找作为“类型”的建筑实例,依靠城市场景的拼贴,创造新的城市历史情境。罗西的“类比城市”既是他的历史研究视角,又成为了一门设计工具。在年的“米兰三年展”上,罗西作为主策展人策划了“理性建筑”(architetturarazionale)展览版块。他的长幅“类比城市”(cittàanaloga)由他的合作者阿杜伊诺?坎特弗拉(ArduinoCantàfora)绘制完成[23]。在“类比城市”里,可以找到这些经典的建筑:罗马万神庙;路斯设计的维也纳米歇尔广场的银行,它在图面里的透视关系就是最常见的从广场拍摄它的角度;彼得?贝伦斯(PeterBehrens)设计的德国电器工业公司车间;古纳?阿斯普朗德(GunnarAsplund)设计的斯德哥尔摩图书馆;后面是路德维希?希尔贝西默(LudwigHilberseimer)设计的板楼。所有的建筑都按照为人熟知的经典角度呈现出来,整幅图面都是以建筑作为主要元素进行的历史情境的拼贴(图10)。 图10_类比城市 这种带有模糊普遍性的类型学视角,使罗西的类型学转化常常呈现为历史或是形式的片段,讲求可被移植的形式与空间氛围。罗西当年居住在威尼斯时,乘船出门经常路过公爵巷(Vicolodelduca)。这座建筑转角处的费拉莱特式(Filarete)角柱后来被他直接转化为柏林IBA大楼设计里位于转角的柱状楼梯间(图11)。罗西考察雅典卫城时,在帕提农神庙的柱廊间拍下了明暗相间的场景,这后来又被他运用到实际项目的柱廊空间里(图12)。虚实错落的节奏和形式的氛围,是罗西所理解的荣格式的“类比”思想,这些思想均被他转化为实体的建筑语汇。难怪罗西会认为,一段走廊的形式价值和空间氛围与它位于何种功能的建筑里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活人的居所与死人的冥地都可以使用同样的“类型”。于是我们看到,他在米兰的加拉里特舍住宅(GallarateseHousing)与莫德纳的卡塔尔多墓园(SanCataldoCemeteryinModena)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项目中都运用了相仿的尖顶走廊空间,在这里,走廊成了罗西钟爱的一种“类型”。这些模糊的片段化的场景其实都有各自的历史原型,这就是罗西“类比”视角的出发点。 图11_费拉莱特设计的柱子与罗西设计的柏林IBA大楼 图12_帕提农神庙的柱廊与罗西设计的柱廊 从阿尔干到罗西,“类型”的这种模糊特征给艺术家或建筑师的创作带来了更广阔的历史援引。这种模糊的普遍性让艺术家或建筑师重复“类型”的创作过程,而不是直接复制“类型”。当类型学被罗西等人沿用到城市问题中,它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历史研究,而是试图成为一种设计工具。然而,或如荣格所言,“类比”行为本不该转化出实体,因此罗西借此所谈论的建筑自主性问题,也很可能在理想形式转译历史片段的过程中显得独断和专横。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意大利建筑类型学与形态学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随着塔夫里、罗西受邀到美国访学,建筑类型学进入美国[24]。年,意大利《美丽家居》(Casabella)杂志以“类型学的根基”(Iterrenidellatipologia)为主题出版了一期专刊[25],对过去近20年的建筑类型学做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讨论。其中,罗西在采访中被问道,“我们都知道您是类型学和城市研究的重要发起人,现在您为何不继续进行这些研究了?”我们不妨以罗西的回答作为本文的结尾。“我跟我的同事最开始的研究是想让建筑学的学科框架更清晰,为年轻建筑师提供更多的自由。不过,要是将类型-形态学研究当作建筑学的主流,这很可能反过来又约束了这种自由。功能主义曾经给它自己制造出很多神话,我不希望看到类型-形态学重蹈覆辙。”[26](感谢安东尼?维德勒教授对本文写作的指点。)图片来源:图1,作者自制,源素材来自网络;图2,SaverioMuratori,StudiperunaoperantestoriaurbanadiVenezia,图3,图4,CarloAymonino,LoStudiodeiFenomeniUrbani,Rome,;图5,PierVittorioAureli,TheProjectofAutonomy,;图6,作者根据AugusteChoisy与Viollet-le-Duc的图解重绘;图7,作者重绘;图8,O.M.Ungers;图9,图10,来自网络;图11,图12,安东尼?维德勒在耶鲁大学建筑学院年春《建筑理论》讲座课件注释:[1]阿根廷建筑理论家阿方索?卡罗纳-马蒂尼兹(AlfonsoCorona-Martinez)在其著作《建筑学项目》(TheArchitecturalProject)中评述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是用类型学来研究设计在各种复杂情况下的核心问题。从这个层面上看,模型语言对历史案例的收集就是以穷举的思路为设计提供各种范例,设计行为在亚历山大的构想中更像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艺术创作。[2]值得一提的是,柯洪在文章中指出,科学与艺术分离之后,前现代的手工艺品创作方式对类型或者说范型的依赖在自然科学认知方法面前变得不值一提。“模仿”(mimesis)、“习惯”(habit)等类型学的常见手段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3]德昆西提供了古希腊语“typos”的很多种含义,它们均跟雕塑创作有关。雕塑创作涉及形体塑造,有倒模、制范、挖空、雕琢等各种手段。从一尊雕塑到另一尊雕塑,复制或者重新创造,也存在类似的手段。这种跟塑形相关的词源含义影响了德昆西之后的学者对“type”的重新定义。[4]福蒂(AdrianForty)在《话语与建筑》(WordsandBuildings)中提到,布隆德尔(J.F.Blondel)的《建筑学教程》(Coursd’architecture)、迪朗的《建筑学简明教程》(Précisdesle?onsdarchitecture)等著作里提到类型、种类等类似的意思时,使用的词都是“genre”而不是“type”。维德勒(AnthonyVidler)在《类型的观念:学院式理念的转变(—年)》(TheIdeaofType:theTransformationoftheAcademicIdeal,-)中更细致地考察了“type”在该时期文献里的涵义流变。维德勒明确指出,这个时期对“type”的使用带有明显的天主教神学影响下的新柏拉图主义成分,这为后文关于20世纪60年代这批意大利学者的类型学理论中去新柏拉图主义的倾向提供了思路。[5]该段译自德昆西的《建筑学历史辞典》第三卷的“类型”词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建筑类型学的讨论文献基本上都认同“类型”的源头在德昆西这里。[6]“形”、“型”二字最早见于战国文献。《说文解字》有云,“形,象形也;从彡幵聲。”“型,鑄器之法也;从土刑聲。”[7]阿尔干这篇文章出现在给德国艺术史学家汉斯?赛德梅尔(HansSeldmayr)祝寿的文集中。阿尔干之所以在写给赛德梅尔的文章中谈到建筑类型学,是因为(1)赛德梅尔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巴洛克尤其是关于波洛米尼的研究,已经相当接近建筑里的类型学问题;(2)作为艺术史学家的阿尔干北京哪家医院治白癜风最好北京市白癜风治疗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eiguihuaa.com/mghfz/1435.html
- 上一篇文章: 杨帆高考生物考什么怎么考
- 下一篇文章: 超级管用的花调月经病配方